在《倾城之恋》的大帽子底下,不过是乱世中一对庸俗男女的结合,之所以成为传奇,并不是他们的才貌到了倾城的地步,而是倾城意外地成全了他们,使之成为张爱玲所有传奇中唯一一部圆满收场的。若非这场特殊的际遇,他们的结合竟是如此的不可能。
我看着白流苏在镜子前飞着眼风,做着手势,笑微微地说,你们以为我完了么?早着呢!
为了尽快找到下家,她不是不做作的,一直拿着舞台腔放不下来,一举一动都拗着造型,端着身段,就象对着无型的观众。
即使面前没有镜子,她也知道自己在月光中的脸,那娇脆的轮廓,眉与眼,美得不近情理,美得渺茫。
范柳原心中暗自叫好,怪癖地欣赏她象唱京戏一样的小动作,却又想她变得自然点,自我矛盾的反复无常的,他与她近着远、远着近地过起招来,假话里掺几句真话,虚伪中透点真实,犹如黑暗中的微火,他能有的真心也不过如此。
两个都是自私、精刮的人,都不打算付出真心,只盘算着对方肯出多少,而自己决不肯做那个全额支付的冤大头。这倒合了《危险的关系》中梅尔特伊夫人的猎人理论:男女交往,只要单方面有爱情就足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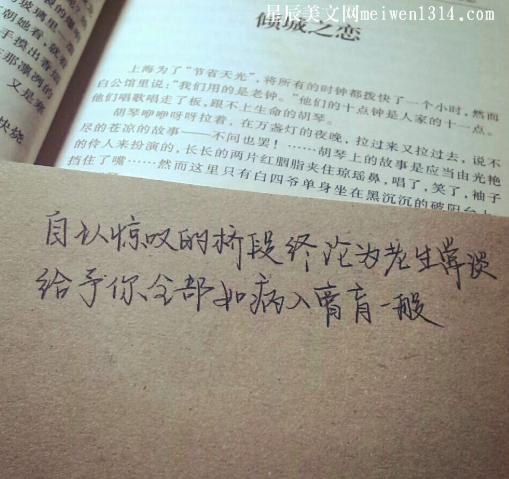
一方享受着爱情的快乐,另一方则享受着取悦于人的快乐。这后一种快乐当然在强度上略嫌不足,但是加上欺骗的快乐,也就达到了平衡。
然而谁来负责欺骗对方呢?两个骗子在时互相认出来了,于是说道:“我们各付一半吧!”然后就撒手不赌了。
白流苏与范柳原这两个赌徒一开始就认出了对方的伎俩,但他们没有谨慎地收手,而是谨慎地投入,因为有一种冒险的刺激,一种惺惺相惜、棋逢对手的快乐。
僵持之后,便是屈服,那种令人难堪的、失面子的痛苦的屈服。现实的窘迫不容她拥有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隔离感与负手而去的清高资格,她只能屈从于范柳原的招唤。
好在范柳原也迈出了入室看月的那一步。一切,还是颠簸着行进起来了。
然后便是战火,男女之间的那些计较都失去了意义,在炮火的轰炸和子弹的呼啸中,唯有象抓住浮泡一般地抓住最靠近的人,潦草地存活下去。
“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他们对于饭食感到空前的兴趣,至于男女,靠得住的不过是自己腔子里的一口气和睡在身边的人。其他的,一切从简。
而这样也算一部传奇吗?奇的是香港的陷落不早不晚,偏偏就在那时,那样大的背景,仿佛单为着让一个小女人得益,英雄简直没有用武之地。
普通的人,不普通的机缘,也便成就了传奇。他们最初耍的那些花枪,费的那些心思,也不重要吗?此城将倾,谁在你身边,却是最重要的。

 狼王梦读后感900字
狼王梦读后感9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