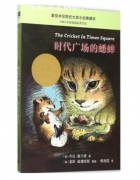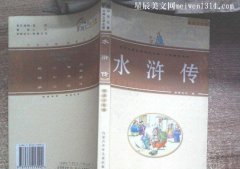于无常处知有情,于有情处知众生。婆娑境里,所有当下动人的故事,全都不是第一次发生。
我的小姑娘,“我的小姑娘噙着眼泪,捧着我的腮帮子说:本来不想的,一看见你就开始想了,现在这会儿最想最想了……”
一个飘荡江湖的浪子,一个骑哈士奇的孩子,一壶普洱、一顶茶壶盖碰撞出一道壮与少、苍白与红稚的缘分。“命丧云南”的玩笑、路平的别样西游回旋着那淳朴的、胜似亲父女的疼爱。两年的时间,不长也不短,足以让一个孩子消弭这个云南;浪子的徘徊,五米的距离,不长也不短,孩子一手搂住浪子,便知这是他的小姑娘。
伴我行天涯,“人生本无定数,回首已是天涯,五味杂陈的劣酒,总好过温敦水一杯吧。”
浪子辗转天涯,阳朔是一个兼容的地方,却不与他兼容。散装的片段散养的回忆,信马由缰而已。他的第一次阳朔之行很突然,端着一碗米粉便上了一班未知的列车。品尝了满是刺的啤酒鱼,沥过全是锋的气刀子,他挎着手鼓捏着羞涩的荷包。夜黑月隐之下,凭借42码的大脸借宿到了一间蟑螂似兔子的房间。手鼓荷包dou遗失在阳朔,事发之后浪子气急败坏。荷包无大碍。关键是手鼓。是啊!那是一对梦幻的见证,见证消亡的纯洁。一杯温敦水递来,回头间,又是一杯。事非当初事,人非过去人。关于阳朔,今朝落笔散文而已。“好比敲手鼓,一首曲子节奏框架在分明,总要有些散排才好听。”酒喝干,又斟满。
此书至此,像一颗流星划过,掀起一道道波痕。书中的江湖缤纷多彩,是每一个心灵最原始的纵马欢歌,使人浮起独身流浪天涯的痴幻。来日纵使千千阙歌,他来自勾心斗角的庙堂,我出身千军万马的学府;他有他雪雨交加的江湖,我有我雷鸣海潮的书案;他归于多元平衡,我自终于将来。先行者在前,赴继者赶往。
我们都将寻究本我。

 读《野性的呼唤》有感800字
读《野性的呼唤》有感8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