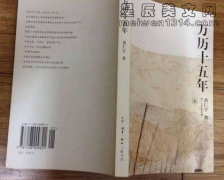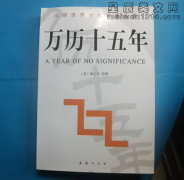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生活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苟且。
两个极为相似的句子,没什么波澜壮阔,也没什么引人深思的道理,但是却传播极广。因为这两个相似的简单句子,精准到可悲地描述了绝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这个绝大多数当然不只是包括我们,就算是远在明朝万历年间,乃至于更遥远年代的古人们,也依旧跳不出这个大多数。他们穷其一生所做的,可能就是在自己的诗和远方以及眼前的苟且中,寻找一个可能从来都不存在的平衡点,以此慰藉自己,从而能在明朝混乱的官场中求得一席之地,而又不必被自己的良心所谴责。
万历年间的首辅申时行可以说是明朝多数官员的典型之一,这位在当时位极人臣权同宰相的大官,历经了各种风雨,从内阁的末尾爬到首辅的位置,期间艰辛不必赘述。按理来说,一个曾经高中状元的内阁首辅,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存在,总该是个很威风的人,但是这位首辅跟他的前任,前前任,前前前任比起来,真是一点都不威风。而因为提拔他的前任首辅张居正在当时的名声已经臭了,因此这位首辅岂止是不威风,甚至是有点卑微。
申时行的历史风评不太好,他在位期间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和稀泥,而这也构成了大多数人对他的看法,大家不认为这位首辅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功绩,以至于很多人都对这位状元持轻蔑的态度。但事实上,一位状元怎么可能没有一点能力?申时行虽然看上去没什么政绩,但事实上,对于当时的官场,他看得很透彻。至少这位任期达八年半之久的内阁首辅,对于当时多数官员的心理状态是了如指掌的。

申时行并非是一开始就是个和稀泥的和事佬,曾几何时,他也怀有打造一个“万历之治”的理想,但是受到皇帝无心礼教,满朝上下都只顾着打着道德理想的名号满足一己私欲的打击后,他的追求终于变成了最低限度的“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对于如何达到这个最低标准,申时行提出了一个理论,也即是官员的“阴阳”,“阳”指的是官员的理想,而“阴”则代指官员的私欲,放在现在,也就与诗和远方以及眼前的苟且有些异曲同工之妙。他指出“阴阳”同时存在,而不论通过任何手段都不可能消灭其中的任何一方。对官员们的本质做了如此简洁而形象的描述,不能不说他对官员们的心理有很深的了解。他通过这个学说得出了一个结论,达到这个最低限度标准的手段,就是调和阴阳。表现出来,就成了“和稀泥”。
申时行的这种发现放在当时可真是一顶一的前卫,他敢于把这种东西说出来实在不失为一种勇气。他对官员的了解之深,无愧于他首辅的名号。应该说他其实发现了自己应该使用的方法,但最后,他的行为却变成了和稀泥,几近是单纯地去满足所有官员的私欲,或是将这种私欲引导向其他的地方。专注于“阴”而不能很好地发展“阳”,专注于眼前的苟且而最终忽略了诗和远方。使得他的行为只能是将隐患埋藏起来,留待他被迫卸任之后一并爆发,表面看起来他的任期风平浪静,但在水面下潜藏的暗流却在一天天地积蓄力量,等待着有一天闹个天翻地覆。
申时行自己并不自知,确实,当时看上去他很好地调和了阴阳,在远方和眼前之间找到了所有人都喜欢的一个完美的平衡,他好像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也就能躺在自己的“远方”自我陶醉。可我们后人再看历史,细细思索,他的卸任,如何不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呢?
申时行的例子,其实可以套用在当时的很多官员身上,他们往往以为自己将事情处理得天衣无缝,认为自己站在大义的一边,站在仁义道德的一边,享受着到达“远方”所带来的愉悦。他们没有想过,“远方”真的是那么容易到达的吗?“远方”真的是可以到达的吗?可惜,申时行本来已经站在了突破这个温柔乡的门槛边上。
申时行代表着蒙蔽自己的大多数。虽然连首辅都沉浸在看似是“远方”的“眼前”之中,但当时的明朝官场或许并不是没有人做到在“远方”和“眼前”之间找到一个最恰当合适的关系。
这个人是个十分出名的民族英雄,那就是蓟州总兵戚继光。
对戚继光的记载其实是毁誉参半的,虽然现在很多人会把戚继光描写成一个完人,但其实仅论操行,岂止远比不上海瑞这样的清官,就算是一般的普通官员(明朝官俸微薄到养不起家,官员弄一点化外收入养家糊口无可厚非)他也比不上。为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求得生存,戚继光会给那时的首辅张居正送礼,礼物应该是很贵重,就算是平时生活比较奢华的张居正也不好意思收太多,象征性地拿一点,然后剩下的还给戚继光,由此恐怕能够很轻易地想象出礼物的贵重程度。稍微了解明朝的人都应该知道,明朝的俸禄低得令人发指,那么如此贵重的礼物从哪里来的,似乎就无需多言了。
戚继光贪了这么多,我们后世还依然把他看做民族英雄不是没有原因的,其一当然是因为他南灭倭寇,北御鞑靼,战功彪炳,其二则是他虽然贪墨,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贪墨的其中一部分实属必要,使他的过错显得小了一点。戚继光在成为总兵的过程中,张居正可谓是如日中天,国家大事虽然有张居正处理,但是在很多地方依然是乌烟瘴气。例如张居正并不反对送礼,其他的官员都送礼,就你戚继光不送,难道是不想要乌纱帽了吗?还是嫌弃自己官阶太高想要低一点?当时的中国,将才很少,几个总兵中能顶用的很少,这时为了保证自己的才能得到发挥,倭寇和鞑靼不会威胁到民众,那么送一些礼物来保证才能充足的发挥空间就情有可原了。而事实上,有了张居正的支持,戚继光确实更好的保卫了边关,而同时又没有利用张居正的信任而谋更多的私利,由此可见,戚继光即使存有一些合理的私欲,其理想是一直不变的,那就是保护民众的安全。这个才是申时行所推崇的阴阳调和,保存部分无伤大雅的私欲的同时,行正义之事。
在当时紧急的军事环境下,内部的一些诸如贪墨之类的事情便显得小了,实在是火烧眉毛。当然,戚继光本人确实可能存有贪墨之心,在这里也并没有为贪墨这一行为辩护,但是史书记载他不事私蓄,那么真实目的到底如何,因为史书中很多自相矛盾的言语,也就显得不甚清楚,因此在本文中不做讨论。
假如我以上的论断还是正确的,戚继光贪污的缘由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话,那么这种错误的行为就还可以原谅。而这就显示出一个在当时环境中的平衡点,也是戚继光可能相信的理论:眼前不得不行的苟且,都是为了远方的诗和光明。在迫不得已之时,为了达到真正的“远方”,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之下,便应该妥协于眼前的苟且,但与此同时,自己的眼睛应该一直看着那个可望不可即的远方,并且保证自己所做的一切妥协都有其意义,同时危害最小。
朱熹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实在太远了。人既然生存在天和地之间,自然不可能事事尽善尽美。与其让一个时代出一两个存天理灭人欲的圣人,剩下的全是市井小民,不如每个人都能达到一个更加简单的标准,让每个人都保留自己的一点私欲,而大体上行正义之事。我们普罗大众,虽然要向着“远方”不懈前进,但也不该对眼前的苟且过分苛责,以至于被自己加诸的苦难折磨,从而只知道抱怨眼前,失去向“远方”前进的动力。
假设能够做到存私欲行义事,可能就达到孔子所谓的“仁”了吧。

 读《伊索寓言》有感700字
读《伊索寓言》有感7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