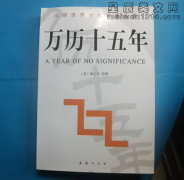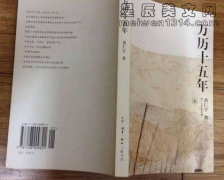没想到,写一个读后感都会这么伤脑筋。
我喜欢历史,但这本书告诉我,我喜欢的只是历史的美貌,只看到了历史长河撞在石头上溅起的水花,却没去想它为什么会撞上去,石头为什么会在那,这是块什么石头。想到哲学上两个名词,我是文科生,高中学的政治,还记得一点,第一句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第二句就是这个量变和质变。万历十五年,或许就是明朝社会量变到质变的最后一步,就像一根长长的导火索,还差一点就要引爆炸弹了。一些人看到了这一点,其中一些人准备踩灭它。但是大多数人没看到,这个大多数是真正的大多数,打个比方,像一个小孩脑袋上的黑头发,准备踩灭的人,就是白头发。万历皇帝,就是其中一根。
书上说过的东西,我不再说,只谈一下自己的感受。读这本书之前,我还是想当皇帝的,虽然没有十七八岁那会强烈。放肆畅想一下,要是当了皇帝,我要住在最豪华的房间,坐在大大的龙椅上,下面的人全跪着跟我说话,我一句话就能决定他们的命运。我要骑最威猛的马,配最锋利的剑,穿最俊的铠甲,东征西讨,战必胜攻必克,走到哪,欢呼声就在哪。我要娶天下最漂亮的女孩,而且是很多个,接下来的话就少儿不宜了,就此打住。但是读完这本书后,我就不想当皇帝了,因为以上所写,大多数不能实现。这个大多数跟上面的大多数一个程度。
首先是日常生活,我得天天早起开早会,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是礼仪大邦,我的一言一行,均有明码规定,稍微打个瞌睡,都会立马有一个快死的老头用极为沉重的方式跪下来,他的膝盖和地板两败俱伤,然后那张皱巴巴的脸上开始流泪流鼻涕,说我不能不能怎么样,然后又说他自己教导无方,罪该万死。我呢,又不能真的让他死,于是就得虚情假意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对着朝廷百官毫无底气却满怀诚意地保证,以后绝不打哈欠。早会上说的事都需要我拿主意,关于国泰民安的还好说,但大多数都是互相打小报告。朝廷都是有党派的,有的是来自同一个地方,有的是出自同一个老师,他们吵起架来,实在头疼。我一个没进过社会的小孩,只能用几千年前的圣人的话,来教育他们。想要讨好双方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要讨好?因为他们动不动就不干了,要辞职回家。他们这些文人,重名轻生,根本不怕死,怕的是不能青史留名。我要让他们死,就如他们愿了。他们青史留名了,我就是昏君了。我要不让他们死,他们就会天天说,我又不能不让他们说,因为明君应该海纳百川,兼听则明。我只是一个小孩,距离找到对付这群老不死的好办法还得很久。礼仪这个事,我时时刻刻都不能松懈,走到哪,有人跟到哪,有护卫,有太监,有宫女,还有记录的。这群记录的人,又是世代相传,他们也属于老不死的那一代,力求完整、如实记录我的言行。我完全没有私人空间,更别说爱好。我喜欢诗词,他们就拿李后主说事。我喜欢练武,他们就拿我一个祖宗说事。那个祖宗我还是很佩服的,尽管我受到的教育告诉我,不能向他学习。朝堂之上的人都长着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他们倒也忠心,忠的是开国皇帝定的规矩,忠的是孔孟之道,忠的是自己的名声,而不是我的喜乐。这一类臣子,迂腐,墨守成规,顽固不化,沽名卖直。他们不懂得改革,只知道用以前的方法来维持稳定。大体来说,他们就是活生生的规矩,像绳子一样缠着我,缠得紧又不至于让我窒息,但仅限我在他们设定的空间内行动。他们不算坏,也很可怜。我只能迁就他们,因为我受到的也是这样的教育。但是另一类大臣,则很有想法,很有能力,他们有力气也有办法,去干我干不成的事,去干别的官员不想干或者干不了的事。他们全心全意的忠心于这个国家,力求国家的繁荣昌盛,想为人民做点事。他们竭力清除一切阻碍,或直接,或间接,或大战,或小动。他们只需要我点头,签字,盖章,其他的事放心就行。我喜欢这样的臣子,替我分忧。但是其他人不喜欢,因为其他人的无作为衬托出这些人的功劳。而且,凡是改革,必定有利益受害的一方。所以利益受到侵害的一方,就会从一些细枝末节,或者改革中处理不当的事,来找茬。他们hai非常擅场利用我二十岁这个年轻气盛斗志昂扬的年纪,告诉我那些能臣“窥窃神器”,意图不轨,这一说,我人性上的弱点也就出来了。我开始多疑,猜忌,做出一些自以为正确的决定,而那些能臣一旦反对,势必恼火我。于是关系愈来愈差,再来点煽风点火,则使得那些人身败名裂。以后的人回忆起这件事,便给我昏君的名号。可若我完全听之任之,成就一番权臣,我又会担心自己大权旁落,受人掣肘,成为一个傀儡皇帝。而且我很难看出这其中的进度,生怕某天一起床,发现连门都出不去。还有一种臣子,就是身边的人,比如宦官。宦官制度自先秦开始,第一个出名的大太监就是赵高。这个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皇室血统的纯洁性,因为皇宫里,正常的男子只能是皇帝,所以有怀孕的,基本上就可以断定是皇子。但是不完整的男人,心理上多多少少也会有些不正常。历史上宦官误国的事件屡屡皆是,而且大明王朝也遇到过魏忠贤这样的大贼。皇帝当然知道这些事,可他依旧信任身边的宦官,因为他们一起长大,朝夕相处,而且宦官总是顺着我的意来,不像那些酸儒大师,教我皇家德行。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是最开心最自在的,他们帮着我跟所有想限制我的人战斗,如果输了,他们也替我受惩罚,而且毫无怨言。再者出于生理上的同情,他们大多因为家境贫寒不得已割身入宫。我们是两个极端的阵营,在皇宫里,我们势单力薄,所以我们结合起来对抗那些满口国家社稷的人。再者,他们就算权力再大,也不会取我代之。是个人就会贪图权力和金钱,他们因为身体上的缺失所以更放大了这方面的欲望。

至于张居正,就是那种特别精明能干的人,智商情商都高,韬光养晦许久,才初露峥嵘,首先把朝廷大臣收拾得舒舒服服的,然后把地方上也收拾得舒舒服服的,我就只需要做那种点头签字盖章的皇帝就行了,然后得一个任用贤良的明君名声。我应该跟他同一个阵营,矢志不渝地相信他,放权给他。他也是那几根为数不多的白头发。但想把白头发薅掉的人太多了,再强大的一个人也没办法顶住其他全部人呕心沥血不择手段甚至愿意以命换命的持续不断的攻击。而且是人就会有纰漏。而这个纰漏就被有心人不断撕扯大,以及其蛮横不讲理的方式把这件补天的布撕得粉碎。皇帝也扛不住,一想到第二天开早会,又有几个老不死的跪在那用鼻涕眼泪吵架,甚至还会动不动。一头撞在柱子上。那些人真是不怕疼啊。可是皇帝看着难受,吃不下早饭午饭晚饭,更睡不好。所以皇帝屈服了,他临阵倒戈,变成了黑头发。张居正心灰意冷,身败名裂,被拔掉了。
我不知道这本书是不是想告诉我们,不要去做那种大多数人不支持的事情。万历皇帝在张居正倒台之后,逐渐看到这一点。天下人需要的只是一个固守传统的君王,只是一个国家象征,是一个只会点头签字盖章的人,一个没有太多想法不去渴望自由的人,一个服从大多数人的人,一个听话的人。张居正有能力也有信心去做一些国家社稷黎民百姓需要的事,他收拾得了朝廷里的其他大臣,却对几千年的孔孟之道无能为力,对朱子思想的根深蒂固无能为力,对大多数明明知道现状不对却不想改变的人无能为力。他输在孤掌难鸣,输在不服气。不知道他会不会后悔。要是只做一个守成之臣,申时行那样的,仅仅是从中调剂,就事匡维,力求和衷共济。他们当官的根本在于防止坏事发生,而不是大刀阔斧地去解决问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样的屁话,简直就是擦屁股的纸。
申时行,彻彻底底的大好人,特别擅长调剂折衷。如果说张居正是万历朝的建筑师,他则是大裁缝,到处修补。古人这么说,“泊然处中,重国体,惜人才”。他谁都不愿意得罪,向上讨好皇帝,向下讨好众人。一旦皇帝和众人有了矛盾,他就里外不是人。刚好也就出过这么一回事。万历想立自己喜欢的女人的儿子当太子,不是长子,不符合规矩,所有人都反对。一旦大多数都反对,皇帝也就失去了皇帝这个身份的权威,因为他的权威,仅仅来自于大多数人都赞同的事。百官联名上奏,必然要拉上首辅申时行。而皇帝以为申时行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不说赞成,起码不能反对。这些都是书里的事了,细节处自己去读。我想问的是,当老好人究竟好不好。写到这越发觉得文人是个可怕的东西,其可怕之处在于他总能找到光明正大的理由来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而这些理由,又来自大多数人认可的权威性著作。直说,就是孔孟朱子。文人的可怕在当官之后得到了升华,变得更加可怕,而且可恨。他们心里的物质欲望跟嘴上的道德标准相差不远,越是以圣人要求自己,越是强烈地追求名利。而且这种心理特征、行为特征被大多数文官群体所认可。这个时候,就出来一个例外,来揭露这群人的嘴脸,来挑战整个文官群体的言行不一。这个人就是海瑞。
海瑞是个大清官,清到比老百姓过得还清贫。闭上眼睛想一想,他应该是整个官场最瘦的人,很可能还营养不良。他始终一副耿直不屈的样子,力求公正廉明,忠于国家,孝敬老母。他的生活一丝不苟,一举一动都符合圣人的规范。他不贪财不图名不好色,没有什么兴趣爱好,每天起床的动力就是做一个好官,为百姓谋福利,需要舍己为人的时候,他绝不推辞。官场里的阿谀奉承,上下逢迎,他不屑一顾,并且带着最原始最纯粹的圣人之道去挑战乌烟瘴气的官场。文官群体找得到张居正的纰漏,却找不了海瑞的茬子。然而海瑞的名声已经为广大老百姓所知,他们若是对海瑞不利,则舆论上过不去;但要对海瑞听之任之,则势头不妙。所以只能把海瑞放在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海瑞也是一根白头发,而且相当刺眼,刚好长在脑门上,挺拔坚强。他是个清官,但不一定是个好官。这话说得很难受。海瑞的德行操守,忠孝无双,估计连孔孟朱熹都比不上他。他严格按照圣人的言语要求自己,身体力行,凡事都有规矩。如果说皇帝身上的绳索是被文官群体套上去的,那海瑞身上的绳索,不仅是自己拴住了自己,还栓得很紧,而且他享受其中,可以不断再瘦一点,以便再紧一点。他为官的基石是在于他的道德标准,力图以身作则,并坚持为百姓干好事干实事。他自身能力有待考究,但只是单纯地用圣人之道来管理一方事务,难免会遇到一些难堪的事情。这些都可以忽略,或者已经被忽略了。我们只需记得海瑞的为官清廉就好。
戚继光也是一根白头发,而且这根白头发比所有的黑头发都要挺拔有力。大家都记得戚继光抗倭的事,是民族英雄。历史没有如果,还好没有。印象深的是,当时倭寇几十个人,就在东南沿海一带到处烧杀抢掠,结果还能全身而退。这种事,在北方是马上民族常干的事,但毕竟也是内部纷争。倭寇这事,就说不过去了。在那几百年后,同样是喜欢进攻的北方少数民族和海上民族,展开较量,一败涂地。这是后话。我想说的是,关于文臣武将的关系。众所周知,在开国时期,武将地位都高于文臣,动不动好多个大将军,封侯称王,文臣则就是一个宰相一个军师。而到了和平年代,则是满朝的文臣,也就是文官群体——这是一个唇枪舌剑的群体,而且技艺高超,通常就是几句话的事,就能把一场战争打败,就像自己抽了自己一巴掌,然后说,“脸疼点无所谓,身体没事就行”。他们不擅长对外战争,却十分擅长内战。他们总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每天不是担心这个造反,就是担心那个谋逆。他们认为外部的忧患花钱就能解决,大不了丢点面子,但内部的权力之争,绝不可以松懈。或许是受的教育的关系,君子动口不动手,他们厌恶打打杀杀,瞧不起那些五大三粗的将军。这些文官通常不懂得怎么打仗,奉旨监军,临行前才补了几课孙子兵法或者三国演义,到了战场上又颐指气使。他们力图挑些毛病,来证明自己深知军事;他们放着白捡的军功不要,却想着出风头。在古代当将军真是件难为的事情,打赢了,遭人妒忌,备受谗言,一不小心就被割了脑袋;打输了,那更不必说,死定了。历代皇帝对武将的猜疑总要高过文官,而且文官群体恰好都十分潜规则似的了解这一点,所以压武将好多个头。除了那种英明神武的跟武将有特殊交情的皇帝除外。戚继光没有遇到能识货的皇帝,却遇到了张居正。成也居正,败也居正。他们命运相似,是聪明人,爬到过山顶,并待了很长一段时间,长到后面的人等不及了,才齐心协力把他们踹下去。问题来了,是不是不管怎样厉害的人,都不会辉煌到头?项羽?关云长?岳飞?
再说李贽。这又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满脑子的不合时宜。他几乎觉得所有现行的东西都是不对的,连太阳都不应该东升西落那样(夸张手法)。鲁迅问,“从来如此,便对吗?”李贽也这样问,回答他的人都说“是啊是啊是啊,听话就对了孩子”。于是听话的他读书当官,但是他脑子里的想法从来没有停过,他觉得不把这些想法说出来,自己就死掉了一半,“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然而祸来又不即来,等死又不即死,真令人叹尘世之苦海难逃也。可如何?”所以同样是死,与其自己把自己憋死,不如敞快一点,都说出来,舒服一会算一会。,他终于想明白了,死在反抗中,更值得。于是著《藏书》《焚书》,明说“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他嘲讽那些道貌岸然的君子儒士,“动与物迕,心与口违”,“把经济上的利害关系抽象升华为道德,比如有教养的人绝不能以利害义,然而一旦接触实际,这种精神常常只是海上神山”(摘自作者语)。他讲经,办学,吸引了一大批受众。这群受众属于那种心里上多少有点不服传统但又不敢反抗的人,见有人说出了他们的心声,于是拥护。我们很多人都这样,深知枪打出头鸟的道理,有什么不服气的地方不敢说。但是一旦看到有人站出来,而且短时间内没有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这才愿意附和。但是那个更大的文官群体害怕了,他们不能不无动于衷,哪怕他们心里有那么一小滴的认可,也不能表现出来。因为一旦不制止,就意味着李贽是对的;李贽一对,他们就错了。然而他们是大多数,真理是掌握在大多数人手里的,或者说被大多数人认可的事才能叫做真理。他们不能放弃已经融化在自己血液里的传统教育,也不允许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糟老头子去挑战他们崇拜了许多年从来都不敢怀疑的圣人。这时候的文官群体就不讲什么“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大道理了,先把李贽关起来再说。可见,文官群体并不是不会动用武力,只是他们不乐意对那些只会打架不会吵架的老粗动武,但非常乐意用暴力去解决他们说不过吵不赢的问题。被关起来的李贽写了一首诗,“名山大壑登临遍,独此垣中未入门。病间始知身在系,几回白日几黄昏”,你看,就是有很多人,明明知道难以善终,但还是去做了自己想做的事。为什么?就是因为想做。世人都要求我们去做应该做的人,却没问我们想做什么事;还是我们忙着去做应该做的事,假装忘了想要做的事。“七十老翁何所求?”自由!
写到这该结束了。我很喜欢这本书,远远地送了好哥们一本。在这书里挖了很多道理,得存起来,放进仓库。给你们看看我的大道理仓库,有爸妈告诉的,有老师教的,有朋友送的,有陌生人给的,有自己捡到的,也有些不明来历的。有时候遇到一个抉择,我就得来仓库找一下,看看适用哪个道理。有时候一个道理能解决很多事情,比如“人生得意须尽欢”;有时候一件事情会对上好几个道理,比如,男子汉大丈夫,到底应该“宁死不屈”还是“能屈能伸”?若是比道理的库存,我们都不是穷人。小孩子懂得的道理不比七旬老翁少,只是我们还没想好用哪个道理去应对哪件事。或者说我们尝试用别的道理解决同一个事会不会有更好的效果,或者我们就是任性地非要用这个道理解决那个事情。你看,你们年轻的时候也不听话,为什么偏偏要年轻的我们听话?且不说公不公平的问题,可能吗?听一个朋友说,他小时候最不爱上补习班,可他现在给孩子报了英语班数学班美术班。不是说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吗?为什么大多数人做的事明明不认可却还是跟着去做了?小时候看的十万个为什么太简单了。

 《围城》的读后感1000字
《围城》的读后感1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