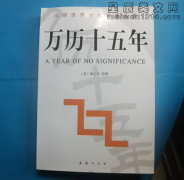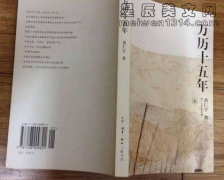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的中国,不见风雨飘摇,也触不到病入膏肓,唯有隐隐发痛的“慢性病”,让人在平淡无奇的日子中,感到些光阴的懒懒流逝。黄仁宇先生用历史学家的视角,文学巨匠的情怀,带领我们凝神此刻的中国, 在时间的温暖里,切开一个断面,揭开曾经的故事。作者截取了从皇帝、宰相、士大夫到六品官员、军事将领、儒家信徒等六方面人物的片段来组成明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的群像,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地展现了明代中国所谓僵化的、保守的官僚体制与落后的、混乱的、零碎的税收管理体系,并以极为个性化的叙事风格刻画了为实现治平抱负而在体制中抗争与灵活变通的人物。为我们摹画出明代建国初始的小农思想与顶层设计,即以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的清晰图景。
贯穿《万历十五年》整部书的一个思想主线就是,西方近代化的技术、组织与制度的理性化、尤其是财政税收体制上的数目字管理化并没有在明代中国发生,而与此同时的西方正处于迈向近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关口。作者一方面是在为中国错失这样的良机而继续沿用传统的老体制不思进取而感到惋惜,另一方面也是在为中国没有走上这条西方式现代化的道路而诊断病因。在作者看来,中国的沉疴痼疾就在于以道德、礼义代法律、以道德代技术的传统思维,而这两项是儒家思想规训下的文官集团的铁律。铁板一块的文官集团在维护祖宗成宪、先圣经训、仁义道德的名义下坚守着他们所认定的“政治正确”,而这背后渗透了多少个人利益的考量与权衡,则是以非常道德化的面目表现的。相形之下,被文官集团裹挟与道德绑架的皇帝看起来陷入非常被动的地位,其所谓的专制权力并没有流俗理解的那样绝对独裁与不受限制。甚至于万历皇帝无奈地选择“罢工”来消极地回应,与整个文官集团作对。无怪乎,明代文官集团会推出像张居正这样的权臣,也会涌现像崇祯这样试图重振朝纲、大权独揽的强势皇帝。可以说,有明一代的最终衰败从一开始明太祖建国所定的基调就被决定了。

在具体的行政管理与社会治理上,明代中国以儒家的道德规训和政治教化代替了技术专家与法律思维。而这是与马克斯·韦伯揭示的技术与制度的理性化、科层化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后者被认为是近代资本主义能够产生以及现代国家构建的关键。“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这是明代从最初建国就定下的基调。作者指出,洪武皇帝所推行的农村政策及一整套的措施最显著的后果是,在全国的广大农村中遏止了法制的成长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作者所选取的极端典型就是被他戏称为“古怪官员模范”的海瑞。一方面,他以极缺乏人情味的严厉法律思维却又推行极为重视人情味的人伦道德,把儒家的忠孝仁义的价值推行到极致,以至于到了违背实情、不顾事理的地步。他所关切的并非事情的是非曲直,而是儒家人伦的道德教化、纲常名教是否能符合圣人所认定的“正确”。另一方面,海瑞又呈现出极为重视规则、不顾人情的理性主义法律思维的一面。不懂得变通与灵活性,对于儒家极为重视的经权问题并没有深刻的领悟。这就决定,海瑞只能作为一个官员楷模的道德典范被朝廷树立(清流),而朝廷所重用的却是一帮深谙权术、懂得现实政治运行法则的更为务实的官僚(循吏)。作者认为,凭借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的个人道德自觉,加之具体处理这些诉讼时的过于自信、自用,而没有任何周密的规章程序以及处理诉讼的专门机构,海瑞注定是要失败的。
作者尖锐地指出,在僵化保守的文人治国的“铁笼”中,也有极个别以一己之力来冲击整个腐朽体制、试图改变保守落后的局面而锐意进取有所作为的英雄。其中之一是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为了施展平生的报复、实现抗倭的大业,深谙现实政治的戚继光知道必须先获得权位,而他选择了一条捷径:直接攀附当时的权臣张居正,通过送名贵礼物获得后者的赏识与欢心。而张居正也是慧眼识英才,重用了戚继光,才成就了明代抗倭的大业。然而,戚继光以一介武夫来试图革新军事体制与设备的努力却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反对而失败。像戚继光这样一位刚毅果敢的卓越军事将领想要提倡新的军事技术、极端军事效率的改革尝试必然失败,因为这打破了整个文官集团所维系的平衡,是与文官集团所要维护的轨道是相冲突的。“现代化的技术和古老的社会组织断然不能相容,要不是新技术推动社会组织趋于精确和严密,那就是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的技术,二者必居其一。”技术、效率总要让位于文人治国与稳定性的考量。在事实上,文官集团只能有一种传统的性格,而由于这个集团是本朝实际上的统治者,他就必然会以自己的性格作为标榜,而责成全社会向他看齐,造成了整个行政的低效。
在税收和财政管理的体制上,明代中国显然缺乏精细的数目字化管理,并且体现了浓厚的农业立国的小农经济思维,以及对工商业的严重抑制。作者以来往官员的旅费这个事例说明财政管理的碎片化与自给化程度,根本没有建立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一杆子插到底的管理体制。按照明律,这笔费用由各大户分摊,根据固定的数字来征收,这样就可以自给自足。甚至就连军队的军饷都不是由国库支出,而是指定应天府的五千个纳税人把它们应交的税米直接送到军士家里。实际上,作者对财政税收制度的批评把矛头对准了儒家思想与文官集团对技术的排斥、抵制以及以道德立国的思想。所谓“君子不器”的儒家思想深刻铸造了传统文官集团的政治性格,那就是在思维上极力排斥与抵制“专家治国”式技术主义的行政方向,而以道德的教化治理国家。因此,这种政治体制设计的目的就不是效率主导,而是以稳定、遵守惯例或成宪为首要宗旨。
然而,作者的视野还是有非常强烈与明显的韦伯理性化理想类型与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明显是站在西方近代化的立场上反观与评判中国。他更多地只是诊断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与政治教化模式的问题,而忽视了这个体制之所以长期延续并成功占据中国人心灵的优点。历史研究已表明,同一时期的西方在财政税收体制上并没有比明朝精确化与高明到哪里去。如果按照马克斯·韦伯对理性化的官僚制特征的描述与定义,比如分工的专业化、名实的相符、非人格化、等级化等标准,中国早在秦代就建立理性化的官僚体制,虽然它远非近代西方那种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建构模式。若是从近代西方传教士的眼光看来看待明代中国,则是另一番景象。传教士们经过观察中国的政治体制后都惊呼中国已经实现了哲人王治国,他们对中国通过科举选拔儒家士大夫担任文官的制度是非常赞赏与仰慕的,并积极地向西方推介。这是因为,“君子不器”的思想早已被孔子深深地刻铸在中国读书人的心中。中国人的政治是培养精通儒家经典的、有深厚人文教养的德才兼备的通才而非技术性专家来教民、化民,这是中国政治的逻辑,它所着力的是安顿人心、立己立人、修己安人的志业。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认为,中国文明从源头起就是一种连续性文明,生产的发展、血缘被地缘取代以至于国家的产生都是由于政治的程序来完成的,而西方则是一种断裂性文明,生产的发展是依靠技术、贸易的突破性提高导致的,因而西方走向了一条向外索取与扩张的技术革新、航海发现、海外贸易的路线。

 野性的呼唤读后感1000字
野性的呼唤读后感1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