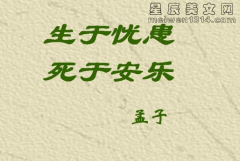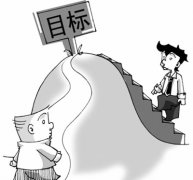本来,自秦代建县后的两千多年,泗阳境内只有两个水系自西向东。一条是六塘河,发源于宿迁,从灌河入海。一条是泗水,发源于山东泗水,流经山东、安徽、江苏后入海。
黄河与泗阳,本是八杆子打不到、挨不上边的。1128年,桀傲不驯的黄河,象一头脱缰的野马,从河南的开封、兰考,安徽的砀山、萧县,一路咆哮,经江苏的丰县、沛县、徐州、邳县、睢宁、宿迁、向泗阳冲来,然后从淮阴、涟水、阜宁、滨海入海。从此,黄河在淮海大地肆虐,直到1855年才改道山东济南、东营入海。
虽然黄河改道,但古老的黄河大堤仍在。它象一条巨龙,静静地卧在那里,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自己的前世今生。沿着大堤,现存的许多地名也在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是怎样的惊心动魄。杨集村有个杨工大塘、城厢镇有个龙门村、新袁镇有个三岔村,还有许许多多。这些地名都和黄河水泛滥密切相关。
更有趣的是,境内有两个同叫龙窝塘的所在。一个是位于李口收费站北侧约500米,这是黄河溃堤冲出的大塘,上世纪六十年代,水面约300多亩,塘水深不见底,岸上有几户陈氏农民专门在此以捕鱼为生,据说曾经捕到百余斤一条的青鱼。另一个龙窝塘位于新袁镇三岔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水面超过千亩,现在尚有500亩左右。这两个神秘的水塘,自生成至今,从未干涸过。
我自小生活在黄河堤下,这里留给我太多太多的记忆。在我的眼里,黄河堤高大威武,七、八米高,望不到头的身驱象巨龙护佑着它的子民;黄河堤又很无私,物产丰富,高大的树木郁郁葱葱,还生长着许多草药,灌木。同时,黄河堤又是非常慈爱,那里的高坡,复杂的地形和众多的树木,是我们儿时游戏的极佳场所,在那备战备荒、时刻准备打仗的岁月,我们也模仿着大人,筑战壕、挖地道。经常小伙伴相约,分成几个战斗小组,舞枪弄棒,各为假想敌,练习打仗。常常是在星星眨眼,月上梢头时分,在家长声嘶力竭地叫喊中,才恋恋不舍地结束战斗演习。

这里,还有发生过一件几十年来经常回味的往事。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未,当时我刚十一岁。
那一年春,妈妈买回一只山羊,通体白色,我的任务是负责牠的生活,自然成了我的好伙伴。每天一有空,我就会牵着它去追逐肥美的青草,不多久,就长得膘肥体壮。
一个星期天的早饭后,我照例牵着小羊,挎着篮子、拿着镰刀,到黄河堤上去放羊、打猪草。初夏的河堤,和风习习,满目碧绿,一片葱茏。高大的洋槐,花蕾初绽,一串串地挂在枝桠上,象一蔟抱团的白蝶;苦楝树上刚刚绽放的白色小花,星星点点,散发着阵阵清香;婀娜多姿的柳树,吐出鹅黄色的嫩芽,修长的枝条,在春风中摇摆。还有桑树、臭椿、柞树等等,都吐出油光水滑的绿叶。用作护堤,贴着地面生长的紫穗槐、公文柳、腊条等灌木,碧绿欲滴,抽着长长的嫩条。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草啊花的,绿殷殷地铺满河堤,这些都是小羊的最爱。我一边放羊,一边割猪草,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小羊差不多吃饱了,我也割了一蓝子猪草。歪过头看了看太阳,我站起身,准备回家。
刚走到坡下,突然听到有人在后面叫我:“放羊的小朋友,你停下,帮我一个忙”。
我转过身来,看到坡上有一个三十多岁男子,他快步走到我身旁,轻轻抚摸着我的头,笑吟吟地对我说:“我平板车胎坏了,要到集上去补,请你帮我看一下瓦。”
黄河大堤上方不到一里路的地方,就是泗阳砖瓦厂。当时县城的机关、工厂、学校等砖瓦都是出自这个地方。我清楚的记得:瓦的一面印有“地方国营泗阳砖瓦厂”字样,当时的砖瓦可是个贵物件。
这个叔叔是到砖瓦厂买瓦回家盖房子的,拉到大堤下坡时车内胎爆了。他把瓦卸下,在路边码好,准备到集上去补胎。但又不放心放在路边的瓦,所以请我给他照看。
叔叔扛起车轮走了,我坐在瓦堆上,一边照看着小羊,一面等待。
等得焦急了,就去割会猪草,再过一会儿又折几根柳枝编个草帽戴上,或者躺在柔软的草地打个滚、晒晒太阳,变着法子稳定情绪。
怎么办?回家吧,一个念头闪出。
大概下午一点钟左右,那个叔叔终于出现了,他走到我面前,拿出用芮草栓着的两根油条递给我。连声说:“没想到、真没想到,对不起、真对不起。”
我摆摆手,挎着篮子,牵着小羊,一溜烟,向家跑去。

 人生的方与圆
人生的方与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