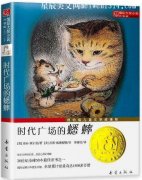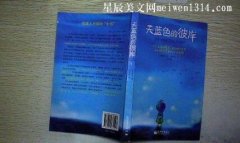“我们的时代没有死亡的艺术,只有救人性命的艺术。”
我相信很多人都对这句话深信不疑,甚至有很多医疗工作者都将其奉为圭臬,但此言的提出者则将其视为时代深深的不安与错误。“真正的存在与现实之间的阉割,是一种难以化解的存在悲哀,那么人们对平静死亡的期盼与现实磨难之间的鸿沟,是否要用虚弱且苍白的双手去做桥梁,然后痛苦地跨过,然后失败,然后再去面对现实?”
有人认为将“死亡”与“艺术”相连接是一种强行文学化的表现,而本书的作者舍温·努兰——耶鲁大学医学院教授用自己完整的行医生涯将这门艺术践行到底。他有着渊博的知识,丰富的临床经验,高瞻远瞩的视野,细腻悲悯的情怀,以其高超的叙述和说理能力成就了《死亡的脸》、《生命的脸》两本巨著。然前者比后者取得了更高的殊荣,从而更加深刻地传递出一种理念——“死亡的艺术,就是生的艺术。活着时的诚实与仁慈,乃是我们如何死亡的真正方法。”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兰亭集序》中:“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均主张执著于当下;宗教中则直接虚构出死后的天堂以寻求精神上的慰藉,然而何以生,何以死?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悲剧是用生命献祭的艺术品,是死亡的赞歌。因为死亡的力量是无穷的,用死亡——生命的结束才更能唤醒人类对人生的深度求索,毕竟生命的意义在于它的有限性,毕竟梁祝化蝶的佳话仍使双垂泪。
将“死亡”等同于“艺术”的说法是不严谨且不正确的,因为“死亡的艺术”更侧重于死亡的“尊严”与“态度”。

舍温·努兰说:“任何阻止死亡的企图都是虚幻的。”由于科技的高速发展而带来误区:“死亡才是最重要的:一场戏剧的主角常是垂死的人,而那位领队来救他的人只不过是旁观者或是配角而已。”或许习惯了太久抢救生命就是医者的天职与成就,但是医者若是单纯地成为疾病的征服者,那么人类通往死亡之途的最后旅程,是否又能得到尊严的对待?书中描写了六种常见的致命疾病,但《阿尔兹海默症》一章在我读过很长一段时间后依旧历历在目且心有余悸,不是因其病情的复杂和研究未果吸引我,而是这种病情给家庭与社会所带来的苦痛是难以言喻的,是让我不寒而栗的,个人的尊严又何值一提?大脑萎缩,神经细胞中出现老年斑块、神经纤维缠结,海马回产生的空泡中含有染色后较深的颗粒,这一切逐渐导致病人记忆力减退、失去理性、理解力丧失,最终失去本能与自发性行为。于是作者写下:“对病人来说,疾病的自然发展就像豺狼一样。但在某些时候,它也许更像朋友。”初始我对这句话完全不解,“朋友”一词从何而来?但当记忆、本能全部消退,意识模糊时,疾病与你形影相随并生死与共,你甚至不能知道这位“朋友”姓甚名谁,这又何尝不是对苦海的逃脱?可念及旧情的家属却无不极度清醒地活着,承受着精神上与经济上的双重打击。在病人病情的末期可能无法克制地走动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需要家属或护工一天24小时的监护;有些可能会变成植物人,而它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的并发症又不由得让家属在病人的生与死之间抉择。甚至在病人生命结束后,家人终于可以长吁出一口气。“阿尔兹海默症是个无情的诊断。没有尊严,受害者的人性被疾病任意和公然的侮辱。”
我们个人渴望追求体面的死亡,“安乐死”有了它出现的原因。我们希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拥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而这种尊严正是根植于我们对待死亡的态度上。《庄子·大宗师》中有言:“夫大块载我以行,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死生亦大,若以生的态度对待死便可获得大的境界。古人汲汲于长生不老,今人亟亟于生命的无益消耗,用现代力量以求生命长度的延伸,可人毕竟也只不过是万千生物中的一种,是大自然的一景一物,终究要在难以抗拒的力量下回归天地,抵抗这种力量只是徒然,用天地万物合为一体的宽广视野就不难体会出努兰所说的“单一个体的悲剧,变成大自然事物的平衡,以及生命延续的胜利”。如此我们便能逐渐形成乐观的生活态度,而这在某些病情的缓解上至关重要,虽并非绝对。
“我听说过许多奇妙的事情/而人类感到害怕的是其中最奇特的一事/明知死,一个必然的结束/它该来时,就会来”,莎士比亚的小诗也适用于当下人的心理。医学提供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病人对医生的期盼值和技术要求就越来越高,索取越来越多。“医学是科学,不是神学,因此不存在百分之百的正确。”努兰在此基础上更强调:“医生不应是疾病的征服者。死亡不是无情的敌人,即使暂得胜利,也值得荒废垂死者曾经耕耘的土地。”医学艺术逐渐湮灭,医学也会面对无助的境地,而医生的一生不仅仅是救人,他们的职责用特鲁多的话一言以蔽之就是“偶尔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在抚慰”。在死亡艺术尚且存在的一个多世纪前,囿于医疗水平,人们尚且可在家人的陪伴下平静地等待大限。在医疗水平发展的今天,医生常用机械、知识为手段而忽视病人的情绪变化,白岩松提出“好医生一定会开‘希望’这个药方”的观点,因为很多病人四处求医无果来医生这里乞求的更是心理的抚慰与平衡。这种抚慰功能不仅体现在言语上,更体现在行为的“细枝末节”上,郁结于心,而发之于外,来自每一位医者对生命的怜悯与尊重。
上述所引用的绝大多数观点大多出自外国人之口,且国外不乏像《死亡的脸》、《生命的脸》之类的著作,韩国更是用电视剧(如《囚犯医生》)直接抨击医疗体制的明争暗斗,这绝非崇洋媚外,而是中国体系的缺失。面对此种现象,本书推荐序的作者中国外科医生李清晨也发此疑问,却欲言又止,意味深长,尽在不言中。不过《白说》中白岩松一针见血,毫不拖泥带水。“当改革不够彻底的时候,医院的目标一度变成了以销售为主旨。不仅患者抱怨,医生也会疑惑,医患关系矛盾重重。”就是由于医生的科研成果与高收入水平得不到制度上的保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问题而导致了医患纠纷;网友对医患关系的受害者幸灾乐祸,出现着对该职业的不了解、不尊重、不包容的现状;囿于病患家庭经济情况等诸多问题,中国的医疗过程也是常常充满不言而喻的苦涩,医者不得不对生活卑躬屈膝,慢慢地沉默下来,谁又敢做第一个发言的人呢?慢慢地靠近深渊,可知深渊也正在凝视你?
《死亡的脸》在其出版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仍为我们叙述着死亡的可怖面孔,影射着中国沉默不敢言的现状。然而也正因它出版于上一世纪九十年代末,其中的医疗知识稍显落后,医疗思想稍显超前,作为一名医学本科生的我在刚踏进这个殿堂前说出这样的观点可能显得不伦不类,但是这本书作为我医学的启蒙,作为我毅然决然选择医学的精神支柱,它的前瞻性依旧吸引着我,让我渴望成长为像舍温·努兰一样求真的人:随着时代的发展,死亡的艺术仍需我们用心、用实际行动去揣摩。理性地认识到医学提供的只是可能性,生活与死亡的必然性皈依于哲学。死亡的艺术就是生的艺术。恐惧死亡,才要了解死亡,从死亡的角度看待生命,才能更好地活在当下。
这或许就是舍温·努兰所传递的真正的“艺术”。

 《铁臂阿童木》读后感
《铁臂阿童木》读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