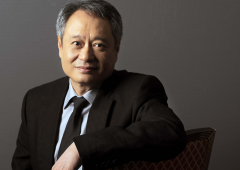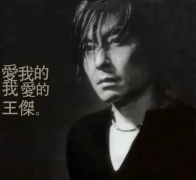他不是厨子,做菜却是专业水准,素菜荤做,荤菜素做,能把白菜做出糖醋里脊的味儿,一道京葱跟海米做的“焖葱”,连汪曾祺都连声夸赞它“盖过所有菜”。
不仅爱吃,爱玩也是从小就玩出了名。弄鸽子、斗蟋蟀、架鹰捉兔、挈狗捉獾,方圆几里找不到他这么能玩会玩的。就连上大学以后,他也没消停过。上课常是胳膊驾着大鹰,怀里揣着蛐蛐儿笼。有次上中国历史课,蛐蛐不安分地叫了起来,气得老师把他赶出了教室。
他不以为意,他用行动证明,玩物丧志和玩物励志之间,只有一线之差。他就是“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王世襄说,他从小就对自己感兴趣的事尤其上心,不但要玩,还要玩得有水平。于是,他花了很多心思来研究这些“业余爱好”。
“玩也要认真玩,如果连玩都玩不好,还能做什么?”
起先他在故宫博物馆工作,后来因为文革变故被“开除”了。
远离了主流意义上的文博界,他不再有机会接近那些他钟爱的文物,却割舍不了自儿时就开始的爱好。
“人生快事莫如趣。”
于是他每天起早贪黑,开始钻研收藏、鸽哨、葫芦等“偏门”学问,并且乐此不疲。风起云涌的时期,他不问政治,常常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与工匠、民俗艺人混在一起。他说人人都有一根“贱筋”,就看长在哪里了。
不论玩乐还是学问,亦或是吃,王世襄都讲究孜孜不倦,勤奋耕耘,虽然兴趣五花八门,做学问也常出旁门左道,但终究凭着这份“讲究”,成果硕然,成一家之言。爱玩鸽子,就把鸽子玩出学问,还撰写了《明代鸽经清宫鸽谱》、《北京鸽哨》等专业书籍。难忘儿时玩蛐蛐儿的美好,就一股脑钻研蛐蛐,写了《蟋蟀谱集成》,堪称一部蟋蟀谱丛书大全。
又迷上装蛐蛐的葫芦,就自己亲手种葫芦。研究中国独有的“范匏”(模子葫芦),还撰写《谈匏器》,呼吁大家重视这一传统技艺,竟让这濒临灭绝的传统工艺绝处逢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的家具都很便宜,很多人都贱卖那些明清家具。王世襄觉得很可惜,在街上看到就买来背回家,还经常大老远跑到附近河北村县买,收集起来堆在家里研究,慢慢就成为了专家。他写的《明式家具萃珍》一书,堪称研究明清家具的经典。
他说:“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的工艺美术——生活习俗,以及游艺情趣等,最能体现中国人的伟大。现在这个北京城,越来越不像过去的老北京了,就是那些故旧的东西、传统的东西,都已经被西洋东西全取代了。我觉得,这很不合理,而且很危险,实在不应该!中国的传统文化需要保护抢救的实在太多了,希望人人都不要数典忘祖才好。”
每件藏品都有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动人经历,王世襄把它们一一着录于《自珍集》中,取敝帚自珍之意,将其中故事娓娓道来,让更多人可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瑰丽。他在收藏这些藏品时,既无显赫的社会地位,又无雄厚的资金支持,全凭自己的学识与眼力,点点滴滴集腋成裘,其间付出的心血非“甘苦”二字可以道出。
夫人袁荃猷的支持,是他最大的慰藉。王世襄编写明清家具研究书籍,有美术功底的袁荃猷就给他画实物线图。夫妇二人经常在一起讨论研究,为了共同的爱好和理想。正是妻子的理解和支持,让王世襄得以更专心地投入到研究之中。后来曾有香港友人愿意出资,购买他珍藏的明清家具。
王世襄开出的条件只有一个:这《明式家具图录》上的80件家具,要一件不留地捐献给上海博物馆。
一个真正的收藏家,对待文物的看法都是聚散有时,而王世襄最终选择了“散尽”。这是一个文物家、收藏家的大开悟、大智慧、大境界。也正是因为王世襄的豁达,这些藏品也有了更多的前世今生。
2000年,86岁的王世襄将自己一生所写的大部分文章交由三联书店以《锦灰堆》为名出版,书中涉及家具、漆具、竹刻、工艺、则例、书画、雕塑、乐舞、忆往、游艺、饮食、杂稿等十二类。
2003年,荷兰王子约翰·佛利苏专程到北京为89岁高龄的王世襄先生颁发“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
他获得此奖项的原因在于,他的创造xing研究已经向世界证实:如果没有王世襄,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处在被埋没的状态。
王先生曾坦言:“我对任何身外之物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只要从它获得过知识和欣赏的乐趣,就很满足。物归其所,问心无愧,便是圆满的结局。”
2009年11月28日,这位自学成才的文博大家,这位穷其一生、玩得专心致志、痴迷不悟、忘乎所以的老人、尽兴而去。

 一个靠捡破烂发家致富的人物
一个靠捡破烂发家致富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