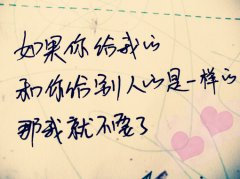我没敢看婶娘冰冻的容颜,只是微微记得她全身肿胀,在冰冷的棺木中间冻的十分僵硬。
我好想婶娘!
我嗤笑她的呆愚,又总是爱捡鸡屁股吃,每次奶奶杀鸡,我吃鸡腿,鸡屁股是婶娘的。
这是我们的约定。
我老往奶奶家跑,婶娘就会看见我,笑嘻嘻的,一口咬下一块大红薯。
奶奶总是爱唠叨,你小时候都是婶娘带大的,为这事她老是和李叔叔打架。
我说长大以后我要养婶娘。
婶娘笑起来像是一个憨憨的猪。
后来李叔叔出去务工。不愿意带着婶娘出去,不喜欢婶娘大手大脚。
那个时候我恍惚之间已经明白了好多的事情,人们每次和爷爷有了过节之后别人总是喜欢骂婶娘是一个二货,没人要的二手货。
我记得金毛是一个狗儿,它老是这个时候叫唤着。汪!汪!汪!
我说婶娘你别管他,这老货见谁都骂人。
爷爷总是在赶集的时候买上一些酒菜,这个时候他总会在村口中大声喊道。
“崽崽儿!去跟你二娘带过去。”
有时候我,奶奶,还有爷爷,婶娘在一起吃饭。爷爷喜欢讲地主老财的故事。
原来我们这儿叫做狐狸屋脊,有个地主叫做周大汉,这周大汉为人十分的甲(吝啬)。总是一副假善人的模样,其实暗地里就是一个扒灰的家伙。
他家是一个高门大院,平常是不会有人敢去的。只是每年到了过节的时候,按照惯例是要请客人的。
只是这一回不知道他家的厨子怎么触到了霉头,在端菜的时候恰恰遇见了周大汉。这人吸着水烟,大拇指上带着碧绿大扳指。看见厨子热气腾腾的门槛肉十分香甜,顿时眼珠一转。趁着厨子不注意在门槛肉山狠狠的吐了一口浓痰。
“刘三,你个背时砍老壳的,肉弄好了没有。”
刘三哈着腰出得门来,却是发现周大汉笑眯眯的站在门后,他急忙将放在桌子上的门槛肉端了出去。周大汉慢悠悠的门槛肉上下的碗打开一看,顿时勃然大怒。
“刘三,你是不是觉得我的工钱开少了,啷个在肉山吐口水,你个扒灰的东西。”
刘三急忙跪在地上发誓赌咒却是没有半点的办法,最后还是求着我家的太爷爷的父亲才放过了他。
克扣了刘三的工钱,还有盘大大的门槛肉,周大汉tian着笑容送走了太爷爷的父亲,吸着水烟回去了。
一别就是一百年,一百年沧海变幻,其中又不知道变化了什么?
那个时候怀着好大的一个孩子!
爷爷不允许家门中出现未有过门便有孩子的女子。
那一年,婶娘生死相隔,两个世界断了她的婚姻之路,断了她的生育之力。
失去了孩子,三个男人,这就是婶娘的前半生。
婶娘喜欢在肉中放上很多的老陈醋,我说婶娘你炒肉放上这么多的老陈醋该干什么。不好吃。婶娘笑着给我乘了一碗米饭。
她说:“崽崽儿,家中没有猪油,只好将就一下了。放多了盐不好吃。”
奶奶年轻的时候赶上了大饥荒,身子不好。吃了很多的药。那个时候怀着婶娘。
婶娘家中有一条狗,狗是我养大的。我叫他肥仔。后来奶奶觉得婶娘一个人在家实在是不安全,就把狗儿送了过去。
肥仔过去了半年瘦了一半!
一年之后,婶娘神神秘秘的来到我家将一大块炒好的瘦肉摆放在我的面前。
“崽崽儿,最喜欢吃瘦肉了,看看好不好吃。”
我尝了尝味道,觉得不是猪肉。
我说不好吃。
婶娘皱着眉头说我已经洗了很多遍了。应该没有味道了。
我立刻警觉的问道:“什么肉?不会是死猪肉吧。”农村有吃死猪肉的习惯。
“狗肉。”
“谁的狗?”
“肥仔被人毒死了。我见扔了怪可惜的,洗了好多遍。”
那一天我不高兴,真的很不高兴。
春耕时分,婶娘想叫我去帮他种田,我不去,爷爷威胁我说不去打死我。
我在婶娘的田埂上咬着野草躺了一天。

我最怕爷爷了。
我嘲笑婶娘一大片水田种了一小片,歪歪扭扭的像是一个蚯蚓。同时不断有摘下去的秧苗浮到水上来。
婶娘骂道:“龟儿不帮我忙。”
我说累,不想动。
回到家之后,我对奶奶说我干了一天的活,好累,奶奶给我煮了三个鸡蛋。
每每想起婶娘背后歪歪溜溜的一地秧苗,眼前总是一个背靠着田坎的少年眼前望着天边的流云.....
我知道婶娘不会怪我的,只是哪儿一地的野草荒芜的有一个人高,婶娘一个人在哪儿艰难的挑着一百斤左右的肥料,肥胖的身躯悄然滴落了一滴一滴斗大的汗水。
婶娘老了!
后来,婶娘家的李叔叔回来了,李叔叔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些水果糖回家过年。
他们在一起吃了过饭,从那以后,李叔叔一直在他母亲的家中。
大年初一我去叫婶娘吃饭,婶娘说不去,我说为什么,婶娘指着水果糖说去了之后那个人会将糖带走的。
她说:“崽崽儿,回去吧,婶娘今年不回娘家了。”
那个时候,我年纪已经不小了,我说婶娘爷爷在家也买了很多的好吃的,有花生,还有大白兔奶糖,还有苹果,好大一个的。”
婶娘不回去,隔着三条田埂的长度我仍然看见婶娘坐在门槛上,怔怔的!
婶娘就坐在哪儿,她挥着胖手说:“婶娘不回去了,婶娘在自己的家过年。”
我最后还是走了,只是婶娘到底守住了那几颗糖,却是失去了一个年。
就在那一年的时候,婶娘开始病了,开始只是吃一些药物,挺过去了就是了。那一会儿婶娘的神志已经有一些不清楚了,只是疯疯癫癫而已。
我对奶奶说:“婶娘出事了。”
是的!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一定出事了。可笑的是我还在安慰自己,事情会变好的。
第四年,那个男人抵不住压力带着婶娘出去了。
回来的时候我看见了在医院打着点滴的婶娘,面色苍白,戴着呼吸罩。
那一年我刚刚读大学,我见到了头发半白的婶娘,将红橙橙的苹果放在那儿,婶娘看见了笑着说:“崽崽儿,买那么多干什么。”
我买了一箱的牛奶,悄悄的将那一些便宜的植物饮料推到了一边。
我说婶娘你以后喝这个,这个是营养快线,这个是特仑苏。
婶娘笑着说:“就是胡乱花钱,别乱买那一些东西。”
我说不值钱的。
婶娘摸着红橙橙的苹果看了又看,叹了一口气悄悄的放下了。
我说我给你洗一个吧,按照往常,婶娘一定会是笑着点头。
只是婶娘眼睛看着窗外寂静的梧桐,怔怔的。
我顺着看过去只见一片梧桐悄然落下。
后来就是军训了,我回家又买了一箱牛奶,婶娘这个时候已经回到了家中。
他看见全身都是泥土的我笑着说道:“崽崽儿,回来啊。”
我说:“嗯。”
她在她家的门槛上,一坐就是一天。
我走的时候给他买了几盒营养快线。
她笑眯眯的缓缓点着头说:“这东西有味道哎,酸酸甜甜的。”
后来三爷在一个寂静的夜晚悄悄的打来了电话:“二娘死了。”
我低低的说道:“知道了。”
那一天我恍惚看见一大片的红薯干,挂在老家的土墙上,婶娘看一下笑一下。
我记得在离开的时候,爷爷叫我去叫村口一个跳大神的神婆。他说你把它叫去给婶娘看一看吧。
我沉默了好久!
答应了!
看着脸颊苍白的婶娘在颤抖的念着:“天父天母之名......”
我撇过头去,怔怔的看着窗外。
流云涣散。
有一回我悄悄的看了看婶娘的一些药物,发现其中只是一些廉价的化疗辅助药物,其中还有一味头疼片。
除去医保,婶娘三年的工钱全部吃了药物了。而医保之下的开销,仍然沉重。
奶奶好多时候笑着说以后婶娘老了没人照顾咋办。
我拍着xiong脯说我在照顾她。婶娘笑起来憨憨的像是一个猪一样。
这就是婶娘的后半生。
沉重而不幸。无法言语的路途艰难难走。可是我知道过去的未来一定有,未来没有的过去一定存在过。
我将大声的悲歌着。
婶娘有一回在门中对我哭,我说婶娘你哭什么。婶娘说地下仍然没有钱花。
我还在学校,婶娘,我哪儿给你钱啊!
婶娘,我改变不了。
崽崽儿没有心的。
我是该批判,还是该沉重的负担。其实我知道,我唯一可以做的或许是改变。
在那一刻我假装平静,其实心中早已苦涩酸楚,是无动的,也是无力的。
即使人xing如此黯淡,即使规矩如此无情,即使我知道贫困是导致愚昧的一切根源。
我还是不想去,不敢去衍生这个世界,我知道那一个个无助的眼神有多大的伤害,那蕴含了人间疾苦的悲悯使我无力回天。那么多的不幸者那么多的悲哀者,无论规矩,无论战争,无论贫困,无论陋习,无论传统。
流逝过去的不止是岁月,还有一快快深深白骨。许多未见得悲伤,许多未见得伤害.....就好像每一次流光之下的生命都化作了凄美的火焰,在一霎那发出的热量温婉而又凄迷。
他们是不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体现。
我能着什么?买几盒奶,或者是请来几个跳大神的神婆。
人世间最凄凉的是莫过于知道结局却是还在一味的欺瞒。
即使勇于战斗于未知,对于命运抗斗而不懈。
可是面对与红尘中的种种流萤,你发现守静的土地长满青草,自己却是以为拥有了一片草原。
实际上,一片荒芜。
最是荒凉。
“背时砍脑壳的。”

 【伤感日志】致那些年,我们错过的男孩
【伤感日志】致那些年,我们错过的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