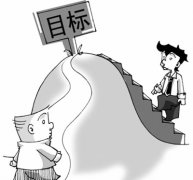知道张恨水的名字是在少年,时值文革,说他的书有毒,想读,然而读不到。俗传他的名字与冰心有关,后见文载: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盖出于此,便觉得雅致。后来在大学里学现代文学,提到了他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等等,似乎入鸳鸯蝴蝶派,可仍然找不到他的书,那是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刚刚恢复高考、读书。再后来大肆出版了,无非风花雪月的诗词和才子佳人的故事,传统章回,觉得不过如此。但是从20世纪的报刊连载小说这个角度看,唯有张恨水和金庸,他们的连载小说都让报纸一纸风行。前年遇到他的散文集,买回家未及细读便置之高阁。近日偶尔看见他的《山窗小品》,清风流韵,叹为观止。
一九三八年年初,为躲避内地战乱,张恨水到重庆加入张友鸾任总编辑的《新民报》,蜗居重庆郊野建文峰下的三间茅屋之中,埋首写作。一九四四年夏,连载小说之余,又有补白似的短文,“乃时就眼前小事物,随感随书,题之曰山窗小品。山窗,措大家事也,小品,则不复欲登大雅之堂。”均自眼前风物生发,点染山水,显影趣味,忧世伤生,文笔似瘠实腴,为不可多得之铭心小品。
文用文言,篇幅短小,文字隽永,在平凡和贫苦中发现生活之美,诗情画意,堪称小品文的典范。意思往往并不复杂,而味道却极为醇厚衍裕。味在视觉、在听觉,也在情感的体验。六朝有不少这样的词语,在后世的书籍中绝迹了,原来在兹薪火犹继。

其时的张恨水,“所居在一深谷中,面山而为窗,窗下列断案,笔砚图书,杂乱堆案上。堆左右各一,积尺许,是平坦之地已有限。顾笔者好茶,案头必有茗碗。笔者好画,案头又必有颜料杯……面对蜂窠,身居鸟巢……于破货摊上,以法币三角,购得烧料浅紫小花瓶一。在乡采得野花,常纳水于瓶,供之笔砚丛中。花有时得娇艳者,在绿叶油油中,若作浅笑。余掷笔小憩,每为之相对粲然。”(《短案》)所居茅屋漏雨,“岁之春,不过数滴,无大风雨,或竟不滴。及暮春,渐变成十余滴。其间有一二巨滴,落地如豆大,丁然有声。数滴更注吾床,每阴雨,被褥辄沾湿不能卧。入夏,暴风雨数数突然来,漏增且大,其下如注,于是屋角,案头,床前,无处不漏,亦无处不注。妇孺争以瓦器瓷盆接漏,则淙淙铮铮,一室之中,雅乐齐鸣。”(《待漏斋》)这待漏斋比之梁实秋雅舍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斯境中,无茅屋秋风号,益显其雅人深致。小品以明清为最,多为闲中所写,而此山窗小品却是在避乱苦境中于长篇连载之罅而为“木头竹屑小文”,殊为难得。
山中风物平常,家国忧思在肩。虽云小品,内中包孕的内涵却林林总总、有大可观处,随手摭拾重庆乡间的寻常风物,如珊瑚子、金银花、小紫菊等山间花草,禾雀、斑鸠与雄鸡一类乡野动物,劣琴、手杖、果盘等人间器物,以及卖茶人、吴旅长、贱邻、农家两老弟兄等寻常人物,张恨水一一描述其仪容姿态、行为举止,比拟绝伦且刻画逼肖,洵谓传神写照。看似跳脱十丈红尘之外,实则别有怀抱在焉。
《雾之美》写:“白雾之来也以晨,披衣启户,门前之青山忽失。十步之外,丛林小树,于薄雾中微露其梢。恍兮惚兮,得疏影横斜之致。更远则山家草屋,隐约露其一角。平时,家养猪坑粪,污秽不堪,而破壁颓篱,亦至难寓目。此时一齐为雾所饰,唯模糊茅顶,有如投影画。屋后为人行路,遥闻赶早市人语声,在白云深处,直至溪岸前坡,始见三五人影,摇摇烟气中来,旋又入烟气中而消失,微闻村犬汪汪然,在下风吠客,亦不辨其出自何家。”(《雾之美》)又一《山市》也。
《虫鸣》:“谷中多草,本聚虫声。而邻家种瓜播豆,菜畦相望,虫逐菜花而来,为数愈伙。每当星月皎洁,风露微零,则绕屋四周,如山雨骤至,如群机逐纺,如列轴远征,彼起此落,嘈杂终宵,加以树叶萧萧,草梢瑟瑟,其声固有如欧阳修所赋者。然习闻既惯,颇亦无动于衷。唯秋雨之后,茅檐犹有点滴声。燃菜油灯作豆大光,于案上读断简残篇,以招睡神。时或窗外风吹竹动,蟋蟀一二头,卿卿然,铃铃然,在阶下石隙中偶弹其翅,若琵琶短弦,洞箫不调,倍觉增人愁思。”
《金银花》:“花状如针,丛生蔓上作龙爪。初开时,针头裂瓣为二,长短各一,若放大之,似玉花之半股,其形甚奇。春夏之交,吾人行悬岩下或小径间,常有惠兰之香,绕袭衣袂。觅而视之,则金银花黄白成丛,族生蔓间,挂断石或老树上。”
读这样的文字,齿颊流香了。
平和,冲淡,闲适,随心随意。素笺锦字,清词丽句。如水泡茶,如茶在水,嫩叶疏舒娟卷上上下下。如山间的草,顺意生长,摇曳生姿。不用正襟危坐,不用焚香沐手,斜倚床头,随手一翻,字字都是清味。唯需有一盏清茶。

 一场白头雪
一场白头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