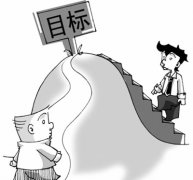好一个大西北,好一个天也高来云也阔!
一座座山,向日葵在阳光里蓬勃着,所有的植物都半是慵懒半是雍容。
青海湖平铺在天蓝之下,周围是白云蜷曲着腻着,还有无边的油菜花海。
走过山,走过湖,躯壳和灵魂仿佛都被这美轮美奂的山水洗净晾干熨烫平整了,没有半丝褶皱。
夜宿青海湖畔“黑马河”,藏民族小镇。
清晨6点32分,我毕恭毕敬地站在湖岸,看一轮朝阳婴儿分娩出母腹般跃出波光涟漪,这时,一行大雁人字形飞过湖面上空,披满金羽。
我继续西行,过茶卡盐湖,过万山之祖的莽莽昆仑。
昨晚,我在黑马河寻了一家小店,左手青稞酒,右手烤羊排,青海湖的水韵涛声陪着我,我的妻儿兴奋而疲惫地陪着我,同天并老地浅酌轻笑。
微醺,踉跄。
茶卡盐湖一片银妆素裹,正应了坊间“若要骚,一身皂;若要俏,一身孝”的民谣,俊俏得紧。
车子以120公里的时速游走在柴达木盆地的戈壁滩,涛走云飞,满帆的顺水又顺风。
一头白牦牛慢慢地前行着,车轮外就是草原,青青黄黄地摇曳着,丰腴又婀娜。
西北的夜,沁人心脾的凉。
我想济宁州此刻多半是又湿又黏磨磨唧唧的感觉,虽说是狗不嫌家贫吧,但舒坦就是舒坦,西北的八月透着爽快。
海拔3871米的拉脊山,也寻常。

敦煌就在西边350公里的那个地方睡着,像它那1600多岁的年龄,珍珠翡翠地堆积着沧桑和福祉。
我明早就去朝拜它,此时,有点儿按耐不住了。
西北的劲风透窗而后撞进我客居的台灯下,好像《书剑恩仇录》里翠羽黄衫的霍青桐深夜撞进陈家洛的书房,撞了个郎才女貌一见钟情。
天还没亮。
告别了月牙泉村,没有犬吠,没有鸡鸣。
出敦煌向东夜行,过瓜洲,想起祖师爷陆游,念着他那年在这里写下的“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走、走得疾。
东方欲晓,我的嘉峪关就立在那里,风采依然。
我伏在城墙上,像五百年前那个尽忠职守的百夫长,左眼凝视着旌旗猎猎,右眼逡巡着芳草萋萋。
我在公元2017年秋天的第一缕阳光里隐隐约约看到了八百公里外的祁连山顶上覆盖的积雪。
我在嘉峪关的城门楼子上趴着发呆,我就瞎想:一年又一年的,只见这草黄了青、青了黄的,饶你是铁打的簪缨冠冕铜铸的棺椁陵墓,什么他娘的紫袍金印拜将封侯的,在时光这座关隘前,啥也不是!
祖师爷里面,我最喜欢苏东坡的豁达和陆游的散漫,尤其是他二位共有的对自己心爱女子的痴痴傻傻的情爱。
大西北,真是个好地方!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