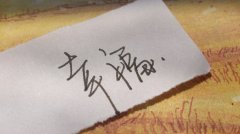武汉下了很多雨。
小时候我老是幻想,是从上个世纪就等在这里的云,这会儿它们终于变成了雨。时间的漫长并不改变某些事物的xing质。不知是什么力量给了它这样足够持久的耐心。我不会有这样的耐心。事实上,在当下的生活中很多人?家丫チ四托摹N揖驮谡庑┟挥心托牡娜酥屑洌胍患枰托牟拍茏龀傻氖?——好好活着。这很滑稽,似乎还有点可叹。

忆起在雷蒙德·卡佛的小说中那些被庸碌无聊的生活折磨得失去耐心的人。他们生活在地球的另一边,伴着卡佛的时代消失了(或许他们的幽灵还活着)。那些失业、破产、酗酒、嗜烟、赌博到处找乐子的失败男人,那些同样酗酒、唠叨、神经质、也是在失败中不断转过身、张开腿以为就能完事的女人。他们在一个个故事里出现,又在一个个故事里退场。然后他们被称为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卡佛的记忆或极简主义。也许更为准确地说,是一个刽子手编辑戈登·利什手握一把带有极权色彩的屠刀改变的一切——他重新塑造、成全了一个时代的卡佛或是美国文学。这不是我们的记忆,但它已进入到我们的记忆中,并在继续影响着我们的记忆。一段时间以来,面对诸多的卡佛们,像是我们已经无法说出拒绝。我们有什么理由来拒绝呢?我们又能拒绝点什么?这是不能够说清也无法说清的事情。就像卡佛小说中那些无端发脾气或是无端感到孤独被失败的命运追逐的无处藏身的人。那些人没有遮蔽、没有伪装地到场、出现,然后说了一段没头没尾的话,又茫然无措地带着影子转身离去。卡佛什么也没有告诉那些在阅读中试图接近文本的读者,他只是极其简约地做了一番呈现——看吧,一切就是这样,它原本这样。但这是卡佛的心灵之眼过滤后的世界。文学像个婊子一样——就隐藏在一双恶毒的眼睛看到的这一切之后。像镜子去掉了水银。

 我和你不再联系,希望你不要介意
我和你不再联系,希望你不要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