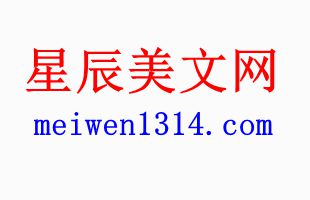小时候,我家里住的是瓦房,一到冬天,冷空气就从瓦缝里吹进来。到了晚上,屋里特别冷。虽然我穿了厚厚的衣服,但还是瑟瑟发抖。这时候,母亲就会用上破炒锅做成的“土味暖炉”,让我们过上暖和的冬天。入冬前,父母亲就已经在为一年中最冷的时间做保暖准备。用破“炒锅”取暖,最重要的材料是大块大块的柴。父亲平时砍下枯死的荔枝树、龙眼树的主干后,会不辞辛苦地从山上拉回家。家里还有很多竹头,这是母亲“积累”的。我家附近都是竹林,有些竹子因为被砍了一截等原因渐渐干枯,最后就剩下竹头了。入冬后,母亲便会到竹林里寻找那些松动了的竹头,用锄头沿着竹头四周锄几下,再拿着锄头敲一敲,基本就可以将其从土里取出来了。寒冬来临前,我家院子里堆着满满一院子,叠得整整齐齐的木柴和竹头,这让我们倍有安全感。强冷空气肆虐的日子里,母亲每天吃晚饭时就将炒锅拿到客厅里,然后准备好柴。她先用竹壳点着火,放到炒锅里,然后迅速放进去竹片或者削得小片小片的松树,能快速让火燃烧起来。充分燃烧后,她就开始加一点大块的木柴进去。放木柴也有讲究,如果放一根,那圆底的炒锅就可能失去平衡,往一边倾斜,所以母亲一般放几根,小心地垒好。有了火气,冰冷的瓦房瞬间就暖和了。“土味暖炉”不仅可以取暖,偶尔也可以充当“烘干机”。在冬天,最怕下冷雨,水寒刺骨,衣服难干。小时候,衣服又不多。每当这时候,在用炒锅取暖时,母亲就会将那些已经晾干了水,但还潮湿的,急穿的衣服收来,在刚开始点火,火烧得最旺时,双手撑着衣服,靠近炒锅上的火,烘几遍,这个一定要小心,要不然,衣服就可能被烧。烘过后,她再搬了凳子在旁边,将衣服铺在上面。所以,我们家常常有一圈铺在凳子上的衣服和我们一起烤火呢。“土味暖炉”还可以充当“烤箱”。取暖时,我常常让父亲放番薯到炒锅里烤。烤番薯可不能心急,不能在火刚烧起来的时候放进去,要有了碳才可以。父亲用火钳将锅底的碳拨开,放番薯进去,然后再拨回来,将番薯埋好。这时候,父亲就要好好控制火势了。等到父亲认为可以了,他就用火钳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拨开上面的碳,再将番薯拨出来。番薯的外皮已被碳烤得焦黄了。知道我急,父亲让我拿碗来,然后用那双布满了茧,好像不怕热的手,拿起烤番薯撕开薄薄的皮,将露出的金黄的,丰满结实的肉放进碗里给我吃。捧着碗,我看着热气腾腾,香气缭绕的番薯,在寒冷的冬夜里,只觉温暖和享受。如今,家里的“土味暖炉”早已退出舞台,但它承载的那些与旧时光,与父母紧密相连的记忆还一直存留在我的脑海里,不会磨灭。

 有深刻哲理的句子,富有哲理或深刻含义的句子摘抄
有深刻哲理的句子,富有哲理或深刻含义的句子摘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