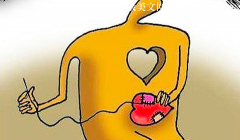不能接受五十岁的事实,却也不能拽住时光的影子,好让它停在五十岁门槛的左边,礼让他人先行。夜里把头仰着吊在床沿外面,想象颈椎间盘突出的三节能被挤压回去。头一摇晃,却发出咯吱咯吱的回声,脖子里响得格外清晰,即刻冒出一股子把它卸下来重新组装的冲动。如果是台机器,我早就把它散开来,清洗润滑,修修补补,滋养包装,按全新的思路组合。摆到人面前时,你定会看到一个模样俊俏的女人,举手投足,优雅从容。可惜,人身不是机器,不是草木,不是随随随便某个物件。她血肉丰满,思维悠长,情感细腻,动一根寒毛能生出细痛,刺一根针尖能染红半边江山。所以,你得好好善待她,她才不会给你意外的打击和致命的重创。
白日里忙成陀螺,鞭子一抽便飞速旋转。转到最后,人不抽你也会转个不停。身体某个部位的响动,即使错位的声音再刺耳,你也不会在意。你是社会里的人,你的出出进进跟社会潮流一起裹卷着滚滚向前。流动是被迫的。带着血腥味儿的惊喜,有一丝痛并快乐的受虐滋味,麻木了神经系统,无论怎样碰撞挤压,哪怕扭曲变形,也会继续被裹卷着滚滚向前。即便偶尔有暖暖的春风吹过,有白如绵羊般的云彩飘过,或是一只恍若隔世的白鹭,伫立在渭河岸边,深情怜惜你随波逐流的狼狈,你的心瞬间诞出生命存在的欢喜,又能如何呢?你会停下来逃离人群,躲进茫茫无边的深山老林,寻得一方无尘的宁静么?
不能!怎么可能?现在,躺进夜晚的浓密墨色里,听脖子里的骨节疙里疙瘩地响动,就会想到隔世的情景。那时,长成一棵没有情感的草木,不会为情所困,悄悄地扎根在某个山涧,汲取一眼清泉,清明地朝着蓝丝绸般的天空,释放深绿色的养分。来来去去的飞鸟,栖落下来也只是瞬间的践踏,把一树枝叶的阳光踏出斑驳陆离的碎影,那又有什么要紧呢?喜欢聚成深潭的一汪水,彩虹飞进去,不搅扰原本的清静,只留个美丽的影儿,倏忽一下就消散了。水色还是原初的透明,透明到尘世的灵魂落进去,都能看到污浊的脉络。

不只是颈椎的突出,还有腔梗。我不懂得腔梗的概念。他们说,就是梗的一种,是极其轻微的梗而已。不要在意。梗的症状如何呢?有时头会闷闷的,混沌一团的感觉。没有这个梗,不会无缘无故地生出思维混沌的表征。怕不?不怕是假的。他们说:五十岁了,正常嘛!这个年龄,出现这些身体的症状,很正常很正常。哦,我才想起,都五十岁了啊!对着镜子看,把眉眼扭来转去,看来看去,怎能五十岁啊?
十岁时,看五十岁的男人,那是很老很老的老人,佝偻着背,扛着铁锨,蹒跚去地头给玉米灌水。满脸的黑斑,是阳光持续不断地照射,给白皮肤染上的重重黑釉。二十岁时,看五十岁的女人,趿拉着布鞋,蓬松着头发,眼角窝着擦不净的眼屎。衣襟也不平整,皱皱巴巴,好像刚从炕上滚起来,就提着镰刀进了燥热燥热的麦地。三十岁时,进了小城,看见五十岁的女人躺在按摩床上,按摩师揉来捏去,疼得哼哼哼地叫,我就不xie一顾。好像剥削阶级似的,净剥夺别人的时间与精力。四十岁时,看五十岁的男人,头顶掉光了毛发,光秃秃地亮。坐在暗夜里,不用开灯泡,也能看清楚他起坐的颓废姿势。
如今,站到五十岁的门槛里,摸着身体疼痛的部位,怎么清点都数不清。总想让人揉捏捶打,甚至踩到后背上面,一脚一脚踩下去,疼痛方能减轻一些,身体方能放松一些。没人按摩时,疼痛难忍,取根集市里买来的枣木擀面杖,朝着肩膀砸下去,狠狠地砸,一下一下,肉里的疼痛便被砸得无影无踪。更严重时,擀面杖砸上去,皮肉都没了知觉。医生说:痛则不通,通则不痛。气血淤堵所致也!怎样造成的?长时间坐着不动。坐着不动是生命的常态。批改作业,备课写教案,都是一动不动地坐着。有了电脑,更是一动不动地坐着聊天。迷上写作,总是一个姿势坐到一篇文章结尾。坐过这么多年,坐出了淤堵,坐出了气血不通,坐出了满身疼痛。如果生命再从二十岁开始,能不再坐么?或者,给二十岁的青年人讲,不要久坐行不?不行!他们有干不完的活儿。哪能挤出时间运动来运动去舒展筋骨?
菊姐给儿子结婚,我去帮忙检查播放的视频。没有做好,有一些细节得修改。窄小的工作室里,四五个小伙子,并成一排坐在电脑跟前,屏幕上摆着做不完的视频图片。每一个画面与声音dou要协调,动一处全盘皆动。做视频是件细活儿,容不得半点马虎。他们一边做一边揉颈椎。能停下来吗?不能!揽了人家的活儿,就得对得起人家的信任。菊姐儿子婚礼的彩排两点开始,视频要播放。小伙子坐到电脑前,眼睛紧紧盯着要修改的地方,仔仔细细改动。原本想再提些问题,看着他们摸着脖子揉捏的神情,我便没再吭声。很多时候,我们总习惯给人挑毛病。哪里想过他们背后的辛苦?所以,王征兵教授就不同。他能体谅学生们的苦处,学业考试能通过就让通过,绝不为难任何一个孩子。他说,真正的学问是要在实践中学,而不只是枯燥的理论研究。
生命是单行道,谁都知道。年过半百,到了知天命之年,悟出一些活着的真谛,却为时已晚。身体不能修复到年轻时的骨骼,血脉不能回复到年轻时的旺盛,眼眸不能返回到年轻时的清亮,齿牙不能还原到年轻时的坚硬,双腿不能退回到年轻时的矫健,手指不能生出年轻时的灵动,连思维也跟着迟滞,反应迟钝,记忆力越来越差。频频出入于医院和单位之间,好像增加了一个家似的,过些天不去,竟隐隐地觉得缺点什么一样。见到朋友同事不再问事业与金钱,而是身体如何,心情如何。更加牵挂在世的父母,担心他们的身体,忧虑他们的悲喜。回家的次数比原来增多了,心忽然变得越来越柔软,软得盛不下一件硬伤的事儿。亲人朋友走一个,再走一个,这时,忽然发现,只有活着,才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任务。没有一个亲人能承受你溘然离世的悲痛。你怎能预测,多少个时光之药的治疗,才能愈合他们心里层层叠痂的伤口?
我五十岁这一天,闺蜜会娥的儿子过周岁。她远去青海,临走之前就去了花店,给我订了十九朵黄玫瑰。早晨九点,送玫瑰的人打了八个电话,我都没听到。他哪里知道,我在参加曹老师的追思会,泪水长流。哀乐声里,我想到生命的无常与脆弱,想到一个个死亡与新生。明知生命的逝去是一种常态,但遇到自己身边,生离死别的悲痛还是不能释然。见到曾经的老领导老姐妹老同事,仿佛见到亲人一般,心窝子热乎乎的。纷纷叮嘱着要常常联系,不要几年不见,见到却是阴阳两隔。
人生一世,不只有亲情爱情,还有友情师生情。活到这般年龄,围绕着亲情在转悠,围绕着工作在忙碌,忽略了没有血缘关系却把你捧到手心儿的一帮子师长和朋友,真是薄情啊!那种刻进骨髓的轻暖问候,冬日阳光般黏在生命的光影里,越是走远越是温软,软到想回过头再把那段日子过一遍!

 游龙虎山
游龙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