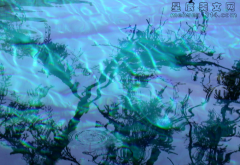有家就有门。
一个村子八九十户人家,各自有各自的门楼。即使是亲兄弟,一分开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筑墙,垒门楼。条件好一点的,门楼弄得高一点,扁砖到地,红瓦漆门。而这也就是近二三十年才有的。
门楼是生活的气象。
在我小时候,凡是看起来高大一点的门楼,大部分为青砖砌成墙基,上面主体墙用土坯垒成,顶上覆盖青色平瓦。当然,还有更气派一些的,但都显得很苍老,门、门框、隔扇都有旧暗的雕刻,在厚的尘土里隐藏着那么一点豪奢。青瓦是弧形的,上下相扣,阴阳怀抱,虽经上百百年风雨,滴水不漏。只有在它上面长高的衰草,经年不除,体现出它的辈分之高,年岁之久。
这样古老的门楼里面,都有故事,都有沧桑。

但大部分人家的门楼,简陋得像他们的人生。细瘦的两根木片,撑起窄窄的门楣,上面草草地放了几片瓦,象征性地为锁钥遮风挡雨。像这样的人家,也有最鲜亮、最辉煌的时光。记得村里有一个光棍,没有父亲母亲,好像荒浊的河流里飘来的一段枯木。他结婚的那天,穿了一件新的蓝色上衣,挂着红布条,小院门上贴着红色对联。我发现他是这么年轻帅气,浑身燃烧着一团火苗。整个院子都亮堂堂,闪火火。然而,这样的日子如同婚衣,婚结完了,穷底也裸露出来。这天新媳妇下地时,我发现她没有结婚时长得高,半边脸还长着一片青痣,丈夫跟在后面,旧绿帽下的脸又瘦又黑又小。几经风雨,红对联被风雨吹打漂白,小门楼低矮破旧,他们的日子紧巴得攥出盐水。只有燕子一样的儿女,在门楼下穿梭,在草纸一样的生活上描红画绿。
我家门楼高大但不古朴,属于中等家庭的那一类。但它确实曾是我的乐园。春天一到,大人们都去地里忙了,他们把我锁在院里,上窜下跳,搜搜鸡窝,逗逗兔子,任其自然。听着小伙伴们的呼唤,为了外面的自由,我只好用手搬,用肩顶,用头拱那沉重的门槛,直到它侧反,给我闪出半尺的空间,我便如知了钻出土地,腾越而飞。还有夏日,太阳把田野烤得变形,我热得无处遁身,门楼之下就成为我的纳凉胜地,厚厚的顶层太阳晒不透,风穿过门洞凉习习,尤其到了吃午饭,捧着被大人汗水浸透的凉面条,坐在门洞下,两腿伸开,头埋进饭碗,吸溜吸溜吞下调了蒜的凉面条,后背汗气蒸腾,其爽无比。当然,最深刻的记忆是春节,是那种下着雪的春节。黄昏来临,父亲披着厚厚的皮袄,脚穿大头皮鞋,踏着雪,咯吱咯吱地走到门楼下,挂起一盏带玻璃罩的提灯,雪缠绕着灯光,踅着身子闪进门洞。父亲念叨了几句,爹哎,娘哎,你们回来吃饭吧,我把灯点着啦,你们不用害怕。
前几年,父亲去世了。回老家时,我会坐在门楼的废墟上,想给父亲点一盏回家的灯,抬头望望,是一片太遥远的天空,和漂浮而过的云朵,灯无处可挂。
我想,就在自己的心里修建一座门楼吧,修一座永不塌掉的门楼,点燃一盏永不熄灭的灯。

 所谓幸福,就是这样简简单单
所谓幸福,就是这样简简单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