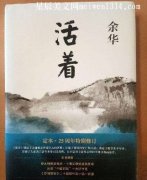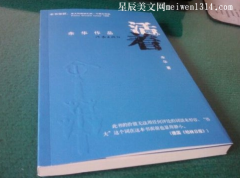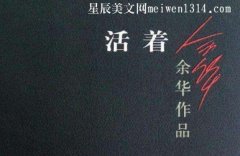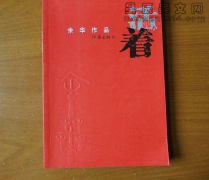前几天和柚子一起下乡时,听说她爱读这本书,读了不止一遍,因此好奇,又加上最近在看当代文学史,所以买来读一读。
小说的开头是一段作者的自白,写他以轻松的心态游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寻找民间诗歌,但是在稻田旁遇到一个叫福贵的老人和他的牛,他坐下来听老人讲他平常又不平常的活着的故事。事实上,我事先没有了解故事的梗概,看到这里还以为整本书都会是作者的所见所闻,而看到“福贵”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才隐约反应过来,这是在讲这个老人的故事。余华的《活着》曾改编为电视剧,名叫《福贵》,在十几岁的电视剧的记忆里,这个?家桓龊苤匾奈恢谩?
福贵原是地主家的少爷,因赌博败光了家产而沦为贫农,然后开始他平常又悲剧的一生,父亲被自己气死,自己被抓壮丁,母亲死于自己离家期间,在解放后的漫长生命当中,有经历了儿子,女儿,妻子,女婿和外孙的相继去世,最后只剩下自己和与自己一样“老不死”的一头老牛相依为命。

书中依次叙述了他亲人的死亡,除了家珍,第二代的孩子们死的都很匆忙,感觉很突兀,仿佛命运注定了他们二更死他们便活不过三更,一切都是命。无论在书中,还是电视剧,最令人震惊的大概就是有庆的死,福贵说:有庆早上出门还是活蹦乱跳的,到了晚上他却浑身冰凉的躺在这里。有庆因为学校组织给县长的妻子献血救命,有庆的血型偏巧契合,为了救里边的产妇,护士活生生的将有庆的血浆抽干致死,却没有任何的法律责任,而福贵一家也无处可恨。有庆死了,谁也没为他们打抱不平,仿佛一切理所应当。这情节里包含的医院对待患者生命的不平等意识叫人心痛,更严重的是在同村人的潜意识里也这样认为。愚昧,势利与逆来顺受在这里凸显的异常深刻。
福贵一生经历内战,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时代,他的生命构成一部新中国农民的史诗,他的土地由个人所有权到交给人民公社,由集体再到家庭联产承包。在福贵的亲身经历中,我看到的是随着时代的潮流以及政策在摸爬滚打的农民,上面制定政策,下面执行,58年大跃进,将农民所有的资产搜刮出来归集体,将所有的锅砸了大炼钢铁,后来在这样的政策维持不下去的时候,上面一句话解散食堂,农民分得的不过几天的食粮,要靠自己解决青黄不接的时段。在福贵年轻时被抓壮丁时曾被困坑道很长时间,靠着天上投下来的大米或大饼度日,那个时候部队的连长告诉他们不用担心,蒋委员长会救他们出去,到最后蒋委员长没来,连长却跑了。他们在坑道里等死,是解放军俘虏了他们,让他们选择是回家还是参军。解放军在那时仿佛一道光芒,救了那些在坑道当中生无可恋的大兵。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时的情景又和那时战争是何其的相似,队长去县里挑粮食,没挑回来,他说国家不会不管他们,一定会送粮食来,结果国家的救济粮食没有来,许多人饿死,许多人出去讨饭,许多人为一个小小的地瓜失去做人的尊严。待到文革结束,上面新的政策下达--分包到户,似乎很合理,事实只是农民从过去的挣扎中解脱出来又开始适应新的挣扎。
说实话,我开始对于新中国建国的三四十年产生了抵触,包括所有人民的处境,农民,知识分子...以及政策等一系列。这些感受来源于像《活着》《牛棚杂忆》这样的文学作品,也来自于当代的文学史。记得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中后面有这样一个细节:季羡林在文革后期已经属于半解放的状态,恢复了一定的人身自由,后来到完全解放时,党组织恢复他上交党费的资格,恢复他的组织活动,但是在他的鉴定表上还是留下了“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文革在后期已经明显是一个错误,知识分子在其中遭受的是不正当迫害,但最后的最后,组织还是认定自己有罪,或许党组织永远是对的。在许多文学作品当中都有对于文革的深切回忆,上文两本书中有,曾经记忆深刻的还有绿原的《绕指集》。(星辰美文网www.meiwen1314.com)《活着》中描写红卫兵进村,问谁是地主,谁是富农,在得知他们都以在解放前死去时,红卫兵不问青红皂白将村里的队长打为“资产阶级当权派”加以折磨,有村民为其说话,被红卫兵说成“不可救药”,在季羡林先生的记忆中,被批斗的场景更是真切,他们就像一群木偶,被拳打脚踢毫无反抗之力。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四年竟也习惯了,对于红卫兵的言论可以做到充耳不闻。
无论十七年,还是文革,留给这一代人的伤痕真真切切看的到,而形成的文风却很一致,他们不大声哭喊自己的冤屈,他们用近乎冷酷的平静的诉说着这段故事。我喜欢这样的语言,喜欢平实的叙说,但我不想经历那样的时代。

 老子道德经读后感
老子道德经读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