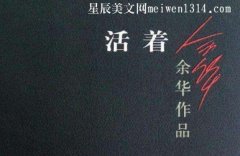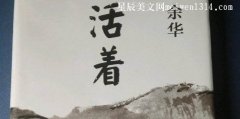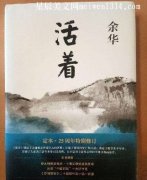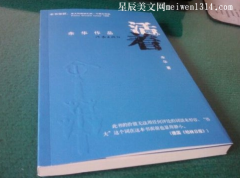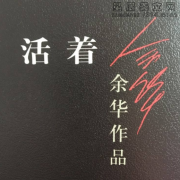《活着》是我近年来十分喜爱的一部小说。当读完这本书,合上书页的时候,那些让人或心酸或温暖的细节仍然萦绕在脑海中:年少的有庆献血救人,却被抽干血,当场死亡;富贵亲手埋葬了有庆,瞒着家珍天天到有庆坟上痛哭;二喜被两排水泥板夹死的时刻,还大喊儿子苦根的名字;最后,只剩下年老的福贵伴着一匹老牛,在田野里孤单地耕种等等,都让我忍不住泪流满面。
《活着》讲述了富贵大半生的经历。年轻时,地主少爷富贵嗜赌如命,最终赌光家业,沦为佃户。父亲被他活活气死,母亲在穷困中身染重病。富贵进城为母亲抓药,在路上被国民党抓壮丁送上战场。枪林弹雨中,富贵侥幸逃生,后来又几番波折回到家中,母亲早已去世,女儿凤霞因为生病成了哑巴。全国解放后,富贵和妻子家珍含辛茹苦抚养一双儿女,但噩运仍然如影随行。为抢救县长的老婆,医生丧尽天良地抽干有庆的血,导致有庆当场死亡。凤霞嫁给忠厚勤劳的二喜,夫妻恩爱,凤霞在怀孕生产时大出血死亡。家珍身患软骨病,长年卧床,在凤霞死后,她伤心过度,过了不到三个月也去世了。二喜在工地被两排水泥板夹死,身体被挤扁,连一根完整的骨头都找不到。七岁的外孙苦根与富贵相依为命,苦根由于过于饥饿,吃了太多豆子被撑死。最终,只剩下年老的富贵,孤独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据说,在创作《活着》之初,余华打算采用第三人称的写作方式,却总感觉写不下去。直到有一天,他突发灵感,尝试采用第一人称,以富贵自已的口吻来叙述,终于思路大开,顺利完成《活着》。叙述方式的转变在《活着》中无疑是成功的,同时也是这部小说的特色所在。阅读《活着》,仿佛亲耳聆听富贵老人讲述自已的故事,原本悲惨的经历,通过富贵老人的感受,所传达给我们的,是满满的善意与温情。正如余华所说:“在旁人眼中,富贵的一生是苦熬的一生;可是对于富贵自己,我觉得他更多的是感受到了幸福。”
评论界把余华迄今为止的创作以时间为界分为“80年代”和“90年代以后”两个阶段。“80年代”的作品暴力而血腥, “90年代以后”的作品则温情和回归生活的真实。《活着》是余华 “90年代以后”阶段的代表作。在《活着》中,余华早期作品中对生活怀疑、绝望的处世态度已消解,呈现的是热情与希望的乐观情绪。

《活着》的语言生动而富有抒情意味,家珍在富贵被抓壮丁回家后对他说:“我也不想什么福分,只求每年都能给你做一双新鞋。”;有庆因不愿姐姐凤霞被送人而拒绝上学:“他干脆一转身,脚使劲往地上蹬着走进了里屋,进了屋后喊:‘你打死我,我也不上学’”…… 诸如此类。相比于语言的诗意,《活着》的情节并不寡淡。事实上,《活着》是将一个历史阶段里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夸张地浓缩到一个家庭中。难能可贵的是,虽然《活着》把人物放在土改、大跃进、文革等特定的社会背景中,小说的立意却并不是渲染社会问题本身,而是着力于表现人性中善的闪光点在灾难面前所闪耀的光芒,这些人性中的闪光点在苦难的衬托下显得尤为珍贵。正如余华在《活着》前言中所说:“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
冯友兰先生认为人生的意义各不相同,人生的境界也就各不相同,由低级到高级,可以划分为四个等级: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富贵的一生也正经历了这四个层次。年轻时的富贵虽然本性不坏,却放纵欲望,吃喝嫖赌样样俱全,此时的他尚处于自然境界。功利境界在富贵身上体现的不明显,或许因为他生性淡薄,也或许因为自幼富足,缺少争名夺利的动力,总之,他极少为功利目的采取行动。唯一的一次是在家业败光后,他打算进城开个小铺子,母亲以“你爹的坟还在这里”为由拒绝,他也就此打消念头,安心作起佃户。
再往上是道德境界。富贵和他家人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这个阶段。春生曾是富贵同一战壕的兄弟,解放后当上县长。正是为了救他老婆,有庆被医生抽血致死。得知有庆的死讯,春生多次上门致歉,都被家珍拒绝,家珍也不许富贵收春生的钱,她向富贵怒喊:“你儿子就值两百块?”但是,当春生在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产生轻生念头时,富贵和家珍却不怕连累,收留他,鼓励他勇敢活下去。家珍终于开口和春生说话:“春生,你要活着。”……“你还欠我们一条命,你就拿自已的命来还吧。”富贵给春生送行时,一再嘱咐他:“春生,你要答应我活着”。春生虽然点头答应,最终还是忍受不了折磨,上吊死了。家珍知道后十分难受,说:“其实有庆的死不能怪春生。”富贵一家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却因为善良的天性,默默做着对社会有益的事,他们是真正有道德的人。
在冯友兰看来,天地境界是最高的境界。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的差别是尽人伦人职与尽天伦天职的差别,也是道德与超道德的差别,即于社会中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与于宇宙中做一个参天地赞化育的宇宙分子的差别。或者说,道德境界中的人,是以人性的自觉行人道;而天地境界中的人,是以天理的自觉行天道;这样,天地境界的人便有了更广大的胸怀与更高尚的气节,他就与宇宙同一,达到了作为人的最高成就。
据说,有一次冯友兰与另一位大哲学家金岳霖偶遇,金岳霖开玩笑地问他,“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友兰回答说:“到了天地境界了。”于是两位教授大笑,擦身而过。
富贵是个只读过几年私塾,贫穷又苍老的农民,从学识、地位上自然无法与冯友兰相提并论。但是,富贵在历经坎坷,失去所有亲人,也失去所有的甜蜜与牵挂之后,没有厌世、沉沦,而是快乐地生活着。当年老的富贵在田野里快乐地耕种时,他已经达到了天地境界,因为人的境界与学历、文凭无关,与阅历、悟性、胸怀有关。
在《活着》最后,余华写到:“老人和牛渐渐远去,我听到老人粗哑的令人感动的嗓音在远处传来 ,他的歌声在空旷的傍晚像风一样飘扬,老人唱到: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富贵唱的,也是他一生的写照。天地境界不同于宗教信仰,宗教是摒弃爱与热情后归于平静,而天地境界则仍然怀着真炽的爱,这是两者本质的区别。因为有爱,所以勇于担当,坦然承受,也因此能够承受生离与死别之痛,并自觉的把爱放大到天地、宇宙间,实现“对一切事物理解后的超然,对善与恶的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世界。”

 实践论读后感
实践论读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