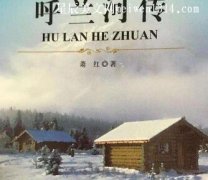对于生的麻木,对于死的麻木,对于一切事情的迂腐都是那么理所当然。粗粝的笔触里写不尽这片土地上无法细腻的人的心灵。如若这里生活的是一群机器也从无这样的荒诞感,可偏偏是一群有血有肉却无灵魂的人,欢喜着跳大神、兴奋着做一名看客,没有人性的恶,仅仅就是愚,愚得令人发笑。永远不会填的坑掉进去的不是鸡鸭鹅猪,是呼兰河人们对自我的欺骗;永远跳不完的大神不是对所谓宗教的信仰,是呼兰河人们对苦难最可笑的抗拒;永远忍不住观看一场场闹剧不是人类美好的求知欲,是生活给可怜的呼兰河人的一些戏谑。

这个落后又闭塞的小城看似简单自然却容不下一个自然之子—团圆媳妇—一个仅仅12岁而被称作14岁的小姑娘;曾经“头发又黑又长,梳着很大的辫子”,曾经“看见‘我’,也还偷着笑”;说碗碟很好看,想坐起来弹玻璃球玩;一点也不害羞,坐得笔直,走得风快,吃饭就吃三碗等。她是一位健康、天真、活泼的单纯的小孩子。因为团圆媳妇不像团圆媳妇—也许是不像呼兰河人心中低眉顺眼的女性奴相—便遭遇“善良”的呼兰河人无尽的“拯救”—暴打、跳大神、公开洗开水澡。直至这自然之子陨落呼兰河的人却唏嘘哀哉自己不幸,没有好运气娶了一个不像团圆媳妇的女人。
长工有二伯,一个呼兰河阿Q,令人可悲可叹,践踏自己的同类,唏嘘自己的命运,又渴望得到尊重。可终究只能是一个只敢对绊脚砖头发牢骚的可怜人。
总得让人在黑暗里看见曙光。冯歪嘴子爱上了王大姑娘,冲破世俗藩篱,不顾他人眼光活成悲壮的模样。冯歪嘴子不算是英雄,可终究算个硬汉,没有一枪柔情,却懂得责任担当。他小儿子露出的一排白牙齿不正是新一轮开始的曙光吗?
这呼兰河小城里的蝼蚁,这呼兰河小城里的人物,这呼兰河里的血和泪,是一首凄婉而悲壮的歌。

 《自控力》读后感
《自控力》读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