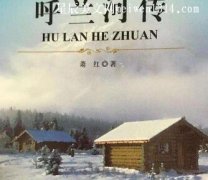这本书是作者的回忆录。我不止是为了看书,还想了解作者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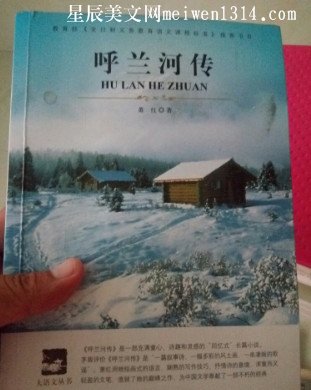
第一章,呼兰河城旧貌。繁华的十字街口,南北方向东、西二道街,有寺庙、学校、商铺,也有大户人家、下人与房客。东二道街中央有一个大泥坑,严重阻碍交通却没人去把它填平,因交通事故多成了大家休闲看热闹的地方。人们事不关己,得过且过。
第二章,当地风俗。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庙会……大都与鬼神有关。人们愚昧迷信。
第三章,作者的家庭关系。严苛的父亲,冷漠的母亲,管事的有洁癖的祖母,有学问又开明的祖父。祖父与作者关系最亲密,是她诗歌的启蒙人。有祖父陪伴的童年生活是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在作者别的书中可以看到,祖父死后她便再无眷恋,离家出走。
第四章,家里房子多、院子大、人少,所以房子都租出去了。于是家里住有养猪的、赶车的,摇摇欲坠的破草房被卖粉条的强租去成了作坊,工人们吃住劳作在一起。为了生计,穷人的命没有其他东西值钱。
第五章,赶车的一家兴衰。先有愚昧虐待,后因封建迷信硬是把12岁的小儿媳给活活折腾死。有觉悟的大儿媳妇跟人跑了。结局是疯的疯,残的残,蛮有生机的一大家子最后落得家破人亡。
第六章,长工有二伯。三十多年的长工资历造就了他扭曲的性格,在老东家面前怯懦卑微,对其他人却又显出莫名的优越感。他临老依旧贫穷,破衣烂衫,开始偷主家东西变卖。大家都知道他偷的事,下人们甚至还当面取笑他。祖父也就是老东家对此却装聋作哑,他对下人的同情对世事的无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幼年的作者。
第七章,邻居家磨官冯歪嘴子。书中除了祖父之外唯一有温度的男人,他对待老婆孩子甚至外人都很客气,但命运却不比他人好一点儿。与他私下相好的同院租客家姑娘为他生下第一个男娃的时候,周围人都嘲笑咒骂他们,在大家的思维里穷人不应该好命。果然,女人为他生下第二个娃以后就死了。究其原因,死于贫穷。
作者萧红,1911年6月1日至1942年1月22日,据此推断,这本书描写的是二十世纪一十年代的事情。看那时,特别是穷苦人们,都在忙着生,忙着死;不念过去,不虑将来,得过且过。绝大多数人仿佛都在沉睡中。
最底层的人们半斤对八两的生活,也不能相互体恤。人家有喜事了诅咒嫉妒,人家有不幸了幸灾乐祸,不幸的事情常常有,于是就有看不完的好戏热闹。
最底层的人里竟还有底层,那就是女人。男人不如意,他就打老婆,所谓娶来的女人买来的衣,任你打来任你欺;婆婆不顺心就打儿媳,所谓千年熬成婆;可悲的是连被打的女人自己也觉得一切都是天经地义,大多都忍着,忍不了的寻死的多,逃跑的少。
对此,作者这样描述,“年轻的女子,莫名其妙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命,于是往往演出悲剧来,跳井的跳井,上吊的上吊。古语说女子上不了战场。其实是不对的,这井多么深,平白你问一个男子敢跳不敢跳,怕他也不敢的。而一个年轻女子竟敢了,上战场不一定死,也许回来闹个一官半职。可是跳井就很难不死,一跳就多半跳死了。”
呜呼!
其实作者本人也算是逃命的女子,但那样的时局,前途必定坎坷,这在她留下的文字中可见一斑。可歌可泣的是,在颠沛流离之中,她仍然坚持创作出了许多优秀文学作品,还得到过鲁迅先生的认可。“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这是历史对她的评价。最后因病早逝,令人痛惜。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儿时的记忆中,村子西北角一个妇人的哭声经常响彻全村,无论白天还是半夜。那是被她老公打的,听着撕心裂肺,人们都习惯了,他们的孩子也不管。据说他们的儿子后来也打老婆,而且青出于蓝还胜于蓝,到现在孙子辈才有改观。
早在1939年7月20日,毛泽东就曾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指出:“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愿人们睦邻友好,愿万物和谐共生。

 《游子吟》读后感
《游子吟》读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