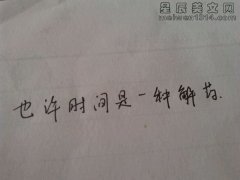初夏的风轻柔惬意,满眼的绿意伴着淡淡的槐树花香,微醺间游离着,手指上的小钻戒闪着夺目的光芒,卧室里传来《斯卡布罗集市》美妙的旋律,这是我的手机铃声。电话那端有醇厚的男中音:“今晚六点绿野仙踪你和元丰咱们不见不散。”“好。”刚要放下电话,突然感觉不对,电话那端嗤嗤地压抑的笑声终于扑哧一声爆发了,爽朗而震撼,我有些发懵,等对方强忍笑意回话时才猛然醒悟,原来是笑我都不问是谁请客就那样干脆地应下了,才顿觉汗颜。其实我一贯是这样,除非确实脱不开身,否则亲朋好友的宴请我一向是来者不拒的。我请客时对待每位亲朋好友都是诚心诚意地邀请,我也相信对方和我拥有相同的心境,准备好了大家要一起尽兴,如果请的人都百般推脱或者干脆不参加,那多扫兴啊。也许我平日里有些安静,但骨子里北方人的豪爽和豁达也是藏不住的。
说到宴请,不知怎么的就想到了妈妈。儿时的印象里,我那心灵手巧善良外向的妈妈常常帮助亲朋好友左邻右舍裁剪做衣服,我家的缝纫机是那个时代的一大件,买得比周围的人家稍早几年,妈妈都是免费地利用时间做邻居的衬衣,亲戚家小伙子的绿的确良军用上衣,张家的格短袖儿,李家的藏蓝长裤等等,虽然很累,但妈妈却毫无怨言乐此不疲。看似xing格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其实妈妈冰雪聪明,做事麻利一丝不苟。虽未学过裁剪却能做出各色美丽合体的服装,有些是妈妈看了别人的服装样子模仿做的,有些是妈妈自己发明创造的,无论哪一种做出的成品服装都令人激动开心,甚至会被要求连做几件相同款式,那时的人虽然也爱美,但有些跟风而不求专版。
妈妈会做各色的鞋子,儿时除了塑料凉鞋我几乎没买过鞋子,妈妈给父亲哥哥们春秋做黑帆布面白帆布边的板鞋,冬天做北京棉——那种黑烫绒面的里面絮了厚厚的棉花,三层的纳鞋底外面包着白帆布,配在鞋的黑胶底上格外精致漂亮。而给我做的鞋子就非常的有趣了,几块小花布角也能拼成一双妙趣横生的小鞋子,宛若工艺品。我穿小的鞋子想要的亲朋好友还真不少,有时不够分妈妈也会动手给他们家的女孩子再做上一双。
妈妈也是织毛衣的高手,各种花样都会,妈妈的闺蜜朋友特别多,冬日里常常坐在我家温暖的热炕上,几位美丽的北方女子切磋织艺,妈妈编制技艺高超娴熟总能帮助大家解除难题,我小时候穿着妈妈亲手设计编织的各种独版毛衣,小伙伴们羡慕得不得了,于是仿版在妈妈的帮助下出现在小伙伴妈妈的手上。

妈妈还会理发,起初是帮小孩子们剪头,其实父亲的头发一直是妈妈剪的,后来有些年轻人喜欢父亲的发型也愿意请妈妈剪头。为了答谢妈妈,常常有人往家里送点儿吃的用的,请吃饭也是常有的。每每有来家里请妈妈吃饭的,开朗外向风趣幽默的妈妈第一时间都会拒绝,那个时代物质极度匮乏,妈妈体谅着人家的难处,心疼着亲朋好友们的不易。请客的人却会拉着妈妈撕扯着不去不放手,妈妈常常是被拉扯得满头大汗浑然无力拒绝了才会乖乖就范,但妈妈是一定要回请的。
那时父亲还是教师,也是我们这一方圆被公认的才子,书法写得特别棒。每年一到寒假,陆陆续续送红纸请父亲写对子的人渐渐多了,当时还没流行卖对联,人们都是买了红纸求人写对联,在当时人的观念里,帮着写对联小事一桩不足挂齿,绝对不会考虑到付费的问题。有些人会裁好红纸送过来,有些人干脆买张红纸送来就走,父亲会把写好的对子晾干叠好再用钢笔写上主人的名字,堆在父亲亲手做的大书架前面等人家来取。每当这时父亲还得事先准备好笔墨砚台和捆对联的纸绳,有时还得帮着裁好红纸,有的人家要求的对联种类比较繁复,父亲就得掂量着怎样才能就着一张红纸而满足人家的春联梦。过了腊月二十,我们晚上睡觉的地方也晾满了写好的对子,于是我们兄妹三个就会被父亲遣送到邻居家借宿,一般要到了三十家里才能清静,这样的义务奉献父亲苦不堪言却从不拒绝,所以别人家都是腊月扫尘,我家腊月是没有时间扫尘的,父亲一般会在三十那天边煮肉边打扫,然后就是匆匆过年了。
对于宴请的态度,我那内向沉稳的父亲态度与母亲却截然相反。正月里父亲几乎天天都被请到别人家做客,有时一天好几家请,只好是谁先来就去谁家。那时没有电话,请客的来家里说明意图,父亲一般是二话不说起来就走,起初是和请客的人并排着走,接着就会越走越快,远远地甩下请客的人而先到到请客地点。宴罢归来母亲都会当着我们的面调侃父亲,这时母亲的笑声总是那样的清脆恣意,完全没有一点儿淑女形象,可是父亲每次都会不厌其烦一本正经地说:“摆席容易请客难,咱别难为人家。我快步先走是为了给请客的主人腾出时间去请别的客人,都像你妈妈那样矜持,请一桌人恐怕得浪费一天的时间在撕扯上吧,那不合适。”小小的我当时会颔首,默认父亲的做法,所以虽然做事如此的内敛而在被宴请时却从不推诿,以至于成了朋友们调侃的话题,但却面无愧色,心怀坦荡。记得有位交好了二十多年的朋友曾戏虐:“咋一接触,极具温柔沉静,定位淑女,内向人士也。熟悉了才发现是话痨,xing情中人,和那张文静的脸对不上号。”
后来想想父亲也蛮了不起的,哥哥小时候癫痫很严重,常常是玩得好好的突然两眼发直,轰然倒地四肢痉挛口吐白沫。这时父亲就会拿出银针给不省人事的哥哥针灸,玄妙的是几针下去哥哥就从那样癫狂的状态恢复正常。我曾缠着父亲问为什么,父亲却说中国的中医博大精深,他也只是自学了点皮毛。因为哥哥是第一个孩子,格外金贵,生下来当天就抽了,当地有一位擅长针灸的女巫医给哥哥针灸了几次,后来哥哥屡屡发病,那女巫医也特别忙不是什么时候都能请到的,情急之下父亲拿着缝麻袋的大铁针试着按女巫医的做法找穴位给哥哥救治,父亲当时的感觉是与其等死不如死马当活马医,结果很神奇,父亲第一次就很成功,抱着复原的哥哥父亲泪流满面,当天就拿了妈妈的银手镯步行三十多里地找一位老工匠打了几枚长短粗细各不相同的银针,又想尽办法买到一本针灸穴位的书,于是开始了父亲的针灸生涯。
那时民风更淳朴些,别人家有孩子生了癫痫病也会来求父亲针灸,有时甚至是寒冬的午夜,父亲都是二话不说穿好衣服带着针具一路小跑着奔赴而去。成年人牙痛,关节痛也会光顾我家,现在想来有点替父亲后怕,可是那时即便没治好也没有人怀疑医生的医术而责怪医生,更不会有医患纠纷的,何况我父亲也不是医生,是大家的认可成就了父亲这位业余医生的。(情感日志www.Meiwen1314.com)后来母亲因为产后风而患的心脏病重了,父亲不但学会了肌肉注射,连吊瓶点滴都扎得很娴熟,基本上一针就成,技术甚至略胜有些专业护士。
父亲还善于化腐朽为神奇,说白了就是变废为宝。记得我家的门坏了,父亲就用菜刀削着从垃圾站捡回来的废包装箱的木板,一小块一小块地拼着竟成就了一扇美丽坚固的房门,进出时轻拉着父亲亲手做的门,心里升腾着无限的骄傲。
如今有些孩子患了癫痫的家长非常担心影响智力,其实不然,我哥哥小时候癫痫很厉害,渐渐长大就没再复发过。后来哥哥考研时竟考了当时他学的那个专业的全国第一名,研究生毕业被名牌大学聘去做了教授,工作后哥哥又考了博士,博士毕业还去了美国哈佛大学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可见智力分毫没受影响吧。而我和二哥小时候都很健康,二哥哥后来当了空军,但读书甚少,跟高智商渊博的哥哥没法比。我也智商平平反应迟钝,师范毕业做了一名小学教师。将就我的智商,整天和学生们打交道还是蛮幸福的,也颇有成就感。

 母亲,从未变老
母亲,从未变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