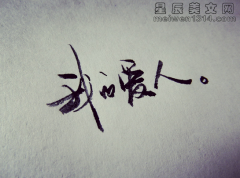下雪就是漫天的样子,没有电影里那么美,飘雪的天大都阴沉沉的,十几个六角小雪花团成一簇又一簇,于是就成了鹅毛的样子。现在想起来,要是真鹅毛,那数量,绝对会让人窒息。摘下手套,让雪落在手上,在体温下融化的那瞬才是晶莹剔透的。
雪是真的白,白到渴了就找没人踏过的地方,捧起一团放进嘴里,是吃软绵冰沙的感觉,加点甜甜的红豆沙应该更妙。等雪下够了,厚厚的堆积在整个世界,才叫银装素裹,一切不美的事物都被它掩盖起来,都像盖了厚厚的白棉被,还把原来鲜艳的颜色衬得更艳。
路上被踩过的雪密实的堆积到一处,变得又滑又硬,既能让孩童踩着火烤过的竹片滑回家,也能让汽车乖乖戴上防滑链。有次买了串糖葫芦,还没咬上一个,就滑了一跤,后脑勺结结实实的磕在雪白但坚硬的路面上,那是眼冒金星最真实的一次。如果你觉得我有时冒傻气,估计就是这么摔的。

天真的很冷,房檐上吊挂着冰瘤子,像守卫的利剑,要悬着整个冬天,等春天才排排跌落。出门去打个酱油,图方便没带手套,不等到家,五指就快没了知觉。冬天上山的大人,回来要先用冷水泡脚。以前不解,直到某天用玻璃的汽水瓶装了烧开的热水,拿到屋外往雪堆里cha,本意是迅速降温,结果却掉了瓶底。可见极冷极热接触的后果有多严重。
雪地里很好玩,坐着爬犁车被大人拉出门是很享受的事情,自己拉着去坡上放,会重心不稳,冲进雪堆,弄的满眼满脸,尤其是那些悄悄钻进衣领的顽皮雪花,冰冰凉凉。放学路上,直接仰倒在路边白色的大棉絮上,留下人形印记。回家就是大人唠叨着脱下弄湿的棉袄棉裤,放在火热的炕头上烘干。
堆雪人是顶没意思的,滚滚滚成一个大圆球而已,早晨家里随便扫扫雪就可以堆出一个。(星辰美文网WWw.Meiwen1314.Com)还是打雪仗来的快乐。小时候有点木讷寡言,参与这种群体活动不多,唯一有印象的是,跟另一个班级不睦,全班总动员的那次,打的欢畅,最后直接抓人往衣服里塞雪,所谓“灌雪肠”。
我觉得长大后能做这么需要讲话的工作,得归功于小时候那些寂静的美丽时刻,让我内心保有最真实的自己,才不至于在言语中迷失。最喜欢的是去河边的制材厂,扒着仓库的门,偷拿些锯好的整齐木片,跑到结冰铺雪的河面,把冰面的雪清掉,做成一个圆形舞台,然后……就是干些傻事呗,属于我的舞台,属于我的秘密,没有观众,没人注视,自由自在的演绎。
陪我这样傻的是一个失联多年的朋友,那时我赖床,每天她都要走到我家,等着我从被窝爬出来,一起上学,再害她一起迟到。放学她会给我讲评书,我听过的第一个评书演员的名字叫田连元,唯一一个评书故事,就是她讲的小八义。也是她教会我《外婆家的澎湖湾》,最后一次见,我还在上学,她已经结婚了,虽渐行渐远,但我还记得她白皙耳朵上的金耳环和依旧爽朗的笑声。嗯,只要看着幸福就好!
家乡还有太多太多的美丽,就到这里,未完待续吧,也许下一次落叶,我还会想起。

 我的青春不后悔,坚持自己的选择
我的青春不后悔,坚持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