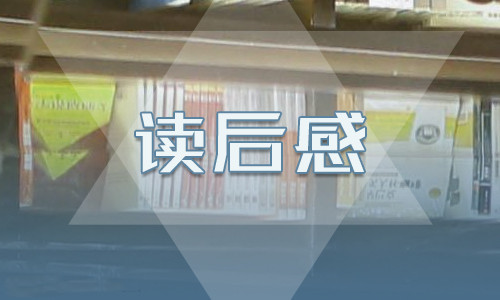有那么一种人,从不管世界是怎样的汹涌,他总是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么安静的坐着,仿佛一切都与他无关。他说,判断那是法学家的事,褒贬那是理学家的事,至于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那是史学家的事。
他都不置喙,他就那么安静地坐在世界的外围。
生活在沸沸扬扬的潮流之外,做彩色世界里的一部黑白片。那是不是缘于内心深处无以言说的孤独呢?孤独,对某些人来说,是一种最舒服最释放的情感方式。有个学心理学的朋友曾经说,孤独与血型和骨骼有关。我一直不能明白他的意思,因为他不是说的血液和骨头。
时常会有这样一种状况,我突然被自己的精神逼到了绝望的角落。我看得见那个角落,是我童年的梦里多次光顾过的。在梦里,每一次我都昂首挺胸执拗地往下走,直到我看到胡同尽头那灰蒙蒙的墙,和墙上甲骨文一样的文字。
梦如果是某种暗示,它是不是告诉我在生活中不要总是执拗于某种状态呢?如果老是那么固执己见,那么生活注定只能是一条死胡同。我想,之所以在梦中那么义无反顾地往下走,或许那一刻我认定那是安全的。一条死胡同里,不会有车来车往,不会有嘈嘈切切。记得一本书上有这样一句话,中心都是漩涡,立于漩涡中随时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像我这种主干神经不够粗壮发达,而末梢神经又过于敏锐的人,只适合徘徊在大千世界的外围。在那条熟悉的死胡同里,我可以随时席地而坐,不会有人来笑话我,更不会有人来打扰我,把“毛病”这一类的词语免费相赠。
在世界认定的外围行走,那是很闲适的流浪,不用担心所有突如其来的东西。地上的水坑,路上的荆棘,都是自然之作。但是,有一种情形是必须有所准备的,那就是,当一个人在外围呆着太久了,他是不是还有在中心生存的能力?人家已经把十八般武艺练得轻车熟路了,随便一招打过来,他有招架之功还手之力?如果不想趟这趟浑水,落得个千疮百孔,那赶紧,哪里来哪里去。如果还想在世界的中心做为一番,那可得冒头破血流的危险。成功,从来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何况还是想在一个敌情没弄清的阵地上硕果累累。
所以,我的地盘就注定了只能是那条死胡同。这么想时,我又对上帝生出了无限感恩。上帝知道,有一类人,他们只需要一条死胡同,来安然度过平庸的一生,刀光剑影,真枪实弹,那不是他们适合的舞台。
有那么些时候,我也会在胡同的墙上扒一个小孔,窥探一下外面的世界。但更多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坐着,对外面的打斗声,哭喊声,争吵声,呻吟声,如若未闻。那是他们的中心,我在他们的外围。
若是换个角度来看,我站在自己的中心,他们在我的外围。我有我的中心,我又何必孜孜于外围的热闹。只不过是,他们的中心是主场,我的中心是界外。虽然是界外,但我与那种被红牌罚下场的全然不同,我根本就没有上过场,我更乐于当个看客。对岸起火了,闹腾着纵火者的窃笑和救火者的慌乱,而我这边是安然无事的从容,只因为我是界外。
当然,如果再站在一个能够“一览众山小”的高处观看,那他们又何尝不是界外。
曾在梦里问过一个奇怪的问题:为什么中心的每一张脸都那么相似?有人告诉我,那是因为那里的每一张脸都是一座城堡。多年来我一直对这一答案抱有怀疑。心想若真如他所说,那所谓的强大,不就只有一堵墙的厚度?后来我慢慢知道,虽然只是一堵墙,但墙里的人却认为这是堡垒。堡垒只容易从内部攻破。我还记得他告诉我答案时,我内心突然恐惧得无法自持,终于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脸,我仿佛觉得它也变成了一座城堡。当我打了个激伶想到我是站在外围的时候,脸又立刻回归到了一张纸的厚薄。虽然依然没有丝毫弹性,依然是那种玉石般的坚硬,但那是我熟悉的温度和质地。

 生活三题
生活三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