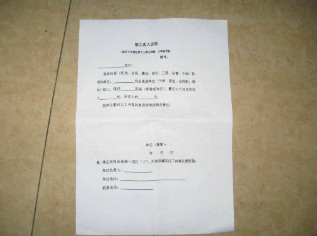有一种病,来势汹汹,叫阿兹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一旦发病就像山体滑坡,一发不可收拾。
我的大舅妈,就得了这病。犹记得,有一次,她吵着让干农活刚回来的大舅给她做“芋头疙瘩”,大舅其实早发现她藏的药,也知道舅妈的病情,却装作不知道,一切如常。大舅赶忙去给舅妈下厨,利落的去皮,剁泥,和面,调汤。大舅妈看着大舅忙碌的身影,那幸福,从眉间溢出来,流到了唇边,扬起了大大的弧度。不一会儿,大舅端上来了,青的透亮的辣椒,红溜溜的西红柿,还有那黄里透白的鸡蛋,在余晖下,闪着迷人的光泽。可舅妈却慌乱的跑去里间,拿出一个红色的笔记本,舅舅98年送的生日礼,用一支铅笔用力的画着,画好,才肯吃。舅舅对舅妈这种行为习以为常,我问他,他却说“不知道。”
看着舅妈风卷残云般吃完一碗饭,大舅忙想再盛一碗,可舅妈却道“我饱了,不吃了。”大舅怕浪费便自己吃完了。
可刚吃完不久,舅妈又吵着要吃,大舅一点儿也不恼,把舅妈因为想不起事情抓乱的头发别在耳后,又开始去皮,剁泥……
做好了饭,舅妈没有立刻吃,又拿出红本子画着什么,画好了,又说不吃了,大舅只得把fan放进冰箱。
有天一大早,舅妈起来,又吵着要吃芋头旮瘩,说话半句一句,不太清楚了。大舅去做饭,舅妈照常望着大舅,只是眼里的泪水越蓄越多,突然跑到大舅跟前,含含糊糊,哭着说“我,我,快,记,不,住,你,了。”大舅忽的一颤,刀切到了手,那鲜血红的刺眼,舅妈赶忙跑出去,满抽屉找创可贴,慌慌张张,把家里抽屉翻了个遍。大舅站在那,晃了神,老半天挤出三个字“在窗台。”舅妈忙起身,抓着创可贴来给大舅贴上。大舅转身继续做饭,一瞬间,觉得大舅的身影多了一丝落寞和忧伤。
饭后,大舅打趣地问舅妈,本子上是什么,舅妈开心的拿给大舅看,只见上面写着赵英志,后面画了好多圈。大舅问,圈是啥意思,舅妈摇摇头不愿说。
在到后来,舅妈彻底不认人。大舅教她拼音汉字,教她认人,教她给鸡喂食,她学的很慢很慢。
她还是每天要吃芋头旮瘩,但说过就忘。每天他做好了,舅妈最多吃小半碗,邻里乡亲劝他放弃。大舅知道,舅妈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但他却一直做,因为每做一次,舅妈就会往红本子上画个圈,每画一个圈,大舅就会开心好久。
舅妈临走前,风和日丽,万里无云,她认真的说“我要吃芋头旮瘩。”“好,我去做。”一切都像是两人刚见面的1968年,他不过给舅妈做了一碗芋头旮瘩,这种爱恋就倾尽了一生。
舅妈走时,大舅没哭。舅妈走后,大舅无论走到哪都带着那个红本子。他卖掉了所有的地,只留下门前那一片,种上最好的芋头……

 女儿的高三
女儿的高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