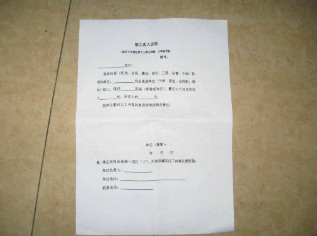到了立夏芒种,农家院子,厨房总是忙碌着家庭主妇的身影,还有脚步在院子零乱响动的沙沙声。她们忙着把刚从菜园买回来的老芹菜,用纳鞋子用的细线麻绳捆绑起来,投放进洗净晾晒过的瓮缸里,然后烧上一锅滚烫冒泡的开水,倒进缸子或半截瓮瓮里,然后用塑料布将缸子瓮口盖严捂实,待过七日,再揭去蒙在缸瓮上面的塑料布,或者木板盖子,酸味钻鼻喷眼。满厨房,满院子飘溢缕缕不绝浆水酸汁香味。
浆水窝好了,这是给辛苦的庄稼汉割麦子、碾场扬麦子消暑解渴吃的。也是苦夏三伏天,家家午饭不可缺少的。过酷热的忙天,,农家饭碗里,离不开浆水面。
早饭刚一吃过,收割麦子的人,挟着木镰,在咣咣咣……上工钟声里,头顶烈日,扑向热浪灼热的麦田。母亲开始在低矮、烟熏火燎、光线有些暗淡的厨房里,在案板上忙忙碌碌着合面、揉面,直到把面揉筋道,光滑青里透亮,母亲这才用湿抹布,把揉瓷实的面团蒙住,放进土灶台瓷盆子里。用手捶捶背、捏捏腰,这才长长吁出一口气。母亲接着择葱胡须上边干枯发黄的叶子,剥蒜皮子,灶房不松不紧的闲杂活,忙得母亲一刻不得空闲。蒜剥的光溜溜,然后用棒棰在碗里捣,把蒜捣烂砸碎,又抹了一把额头,脸上的汗珠。案板上的面团己窝到火候。用抹布把长长明光发亮的擀面杖,轻轻来回一抹,开始哔哩咣当,擀杖与案板亲昵在面团搓揉滚动,发出单调清脆又悦耳的声音,让幽寂静默的农家小院充满夏的活力,母亲喜滋滋脸上堆满笑擀着面。日头正午,在窝里下蛋的母鸡,树荫拉近变小。下好蛋的芦花鸡飞离窝,满院子胀红脸,咯蛋咯蛋前后院叫唤个不停,生怕人不知道它在下蛋似的。
母亲费了浑身劲,擀好一大案板面,用擀杖切成均匀粗细一致的韭叶面,到鸡窝收回蛋,那母鸡才止住了咯蛋声。返回厨房,给少了一个豁口的铁勺,滴了几点菜籽油,把切碎的葱花蒜片放进去,边拉动风箱烧下面水,边燣炒铁勺里少的可怜呛浆水用的下锅菜,铁勺一添上硬杆火苗,四周吱吱咝咝冒着热气。母亲把窝好的新鲜酸浆水,舀进大瓦盆子里,把煵好的葱花往调好的浆水汁里一倒,那十里飘香的葱辛香。很快在浆水汁里循环涟漪扩散,那香味转着圈,在农家院子弥漫不消散。

那时候,我正在离村子约摸四五里外的天度农中上学,我是奔着跑着回家吃母亲做的浆水面。跑得我气喘吁吁大汗淋漓,跑到离城门口快近,老远就看见我家屋顶上空有缕缕炊烟,炊烟里飘浮出的浆水面香,馋得我嘴角吊线涎水涟涟。回到家里,我二话没说,端碗浆水面狼呑虎咽起来。吃了一碗又一碗,肚子发胀还要吃……母亲在我一旁坐着,看我头埋进碗里,一言不发,只是咯咯咯笑个不停。
母亲做的浆水面,从搭镰割麦开始,断断续续吃一个苦夏伏暑,只有到了立秋,天气渐渐变凉的时候,浆水陈旧冒白花,吃不成了的时候,心一横,忍疼倒掉浆水,吃浆水面才算结束。
漫漫时光记忆里,有快三十个年头,沒有吃妈妈手擀韭叶浆水面了。时光荏苒,母亲去世都二十个年头了。每到苦夏,收割麦子的时节,心不由自主飞到老屋,飞到母亲浆水面碗里面,真想再吃一回母亲手擀韭叶浆水面。想吃,都快要想疯了。
前年,公司业务员出差,从甘肃捎带回几包浆水汁,欣喜万分里,我做了几回浆水面,不论我怎么样做,花样变尽,总是做不岀妈妈在世时,那个醇香正宗的老芹菜窝的浆水面味道啊!
妈妈的浆水面,在我记忆的源头源源不断,流淌涌动萦绕缠绵……

 女儿的高三
女儿的高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