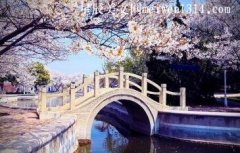在我们这里的农村,没用液化气罐和天燃气之前,煮饭炒菜都是在厨房的灶台上完成。大人在灶台上忙乎的时候,向灶孔里添柴往往就是小娃娃的事了。有时候,爸妈忙不过来,在锅里按比例放好水、米和菜,把烧火煮饭的事就交给我来做。每次,我都满心欢喜地接受任务,因为又可以趁机偷个嘴儿了。
有一次,我对家里的那块腊肉动了心思。添好柴后,我跑到门外喊来坐在地上玩泥巴的妹妹,让她站在门口把风。待三岁的妹妹认真就位后,我走到堂屋小心翼翼地踩上凳子,踮起脚拽住墙上挂着的一块腊肉,使劲切下一小块来。为了不露馅,我威胁妹妹,如果让爸妈晓得了就不给她好吃的。最后还自作聪明地抓了点柴灰,在腊肉白生生的切口处抹了抹。
窜回厨房,我把那小块腊肉简单洗了洗,用火钳将它夹紧递进灶孔。随着腊肉“滋滋”作响,一滴又一滴的油溅落到燃烧的柴火上,蓝幽幽的火苗直向上窜,轰轰几声火势更旺。
手里的火钳抖动翻滚,只见腊肉急剧缩小,不久有浓郁的肉香扑鼻而来。馋得一旁的妹妹砸吧着嘴不停地问,哥,好了没?好了没?给我吃一点嘛。
不晓得,哥先尝一下看看。我取出火钳,顾不上小手被烫得通红,撸下那小块冒着油和香气的腊肉,鼓起腮帮呼呼狠吹几下,迫不及待地塞进口里。吧唧吧唧几嚼,咕咚声伴着滚烫的咸香一下就溜进了肚里,那种滋味简直不摆了(不说了)。

哥,好吃不,我的呢?我的呢?你不给我吃,我要哭啰。妹妹咽咽口水,眼巴巴地望着我,眼泪快要流出来了。我一下慌了神,赶紧安抚说,妹乖哈,不要哭,哥马上给你烤。
……
嗯,香!哥,我还要吃。妹妹一边可怜兮兮地央求我,一边吸着油晃晃的没有了泥巴的小手指。
我的心不禁一软,要得,哥又给你烤……
当爸妈回来时,那块腊肉被我们“糟践”得只剩下大半块,还有小半块黄澄澄的肉皮无精打采地向上蜷着。
妈妈看到我和妹妹大花猫似的脸,再看看我们沾满油渍的小手和嘴唇,好像明白了什么。她往墙上瞅了瞅问,嗯?娃儿们,这肉少了那么多,是不是遭猫吃了?
就是!就是!那只猫讨厌得很。我连忙大声附和,乖巧地使劲点头,额头的汗涔涔而下,同时狠狠地瞪了一眼想张嘴说话的妹妹。
嗝嗝,估计是点头用力过猛,这时几个油嗝不适时宜地冒出来,顿时肉香四溢。好尴尬!我的脸火辣辣的。
哈哈哈,你呀你,你这个饿怂(贪吃)的娃儿。爸妈忍不住笑出声来。
不是我,是妹非要吃的。我看看扑到妈妈怀里的妹妹,小声嘟囔了一句,顺手剔掉牙齿上嵌了好久的肉丝。这下舒服多了,我美美地呼出一口气。不想这口气尚未呼完,肚子里传来“哗啦啦”一阵响。哎哟,我连忙捂着肚子狼狈地往茅房(厕所)冲去,根本顾不上后面更加响亮的笑声。唉,都怪腊肉太咸,喝了好多凉水。
烤腊肉是好吃,可一年就那么几次。这对于当时长期少油寡盐而身体猛长的我来说,显然远远不够。为了满足对肉类的极度渴望,我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心灵手巧:在房前罩麻雀,躲屋后网斑鸠,到田间摸田螺,游河里逮鱼虾,甚至还抓过老鼠和白鹤。这些物什到手后,统统脱毛剥皮、去壳刮鳞,食盐一抹,再洒点藿香粉,皆入灶孔烤之,成为令我垂涎欲滴的美食。隔壁张婆婆曾经开玩笑说,怪不得家里不见老鼠田里没有鱼,原来都被你娃儿抓来烤了吃了。
除了烤肉类,还可以烤苞谷棒、烤红薯、烤胡豆和黄豆……不过,这些东西又是另外一种滋味的美食了。需要说明一下,苞谷棒、红薯等不能用明火烤,要用灶孔里未燃尽的柴灰埋着烤,不然胡了就不好吃了。
直到今天,只要看见有人啃苞谷棒或者吃烤肉,我就情不自禁地满口生津,那种熟悉而美好的滋味穿越久远的时空又来到我的面前。
我想,那种熟悉而美好的滋味,也许已被时光烙印在我的味蕾上,随生而生,永不磨灭。

 乌镇访春
乌镇访春